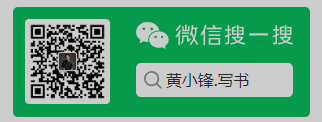「今日小酒馆」那扇有些年头的木门,吱呀一声,被人从外头推开了一道窄缝。
门楣上挂着的那串铜铃,随之晃荡,却只发出一声沉闷的响。
叮铃。
那声响,半点不清脆,反倒像是被这满屋子陈年的酒气给泡软了,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疲态。
吧台后头,付九娘倚着柜子,眼皮便都未曾掀动分毫。
她手里正捏着一方雪白的细绒布,不紧不慢地,擦拭着一只高脚杯。
一圈。
又一圈。
暖黄的灯光沿着剔透的杯壁缓缓流淌,映着她指上那点猩红的丹蔻,划出一道又一道冶艳至极的弧光。
“来了?”
她的嗓音里,是股子猫儿般的慵懒,尾音微微地勾着,挠得人心痒。
“来了。”
应声的,是朱福贵。
一个圆滚滚的身子,颇为费力地从那道门缝里挤了进来,顺势带进一股子初秋的夜风,凉意瞬间便蹿遍了整个屋子。
他一屁股便墩在了吧台前的高脚凳上。
那凳子不堪重负般,沉沉地呻吟了一声。
朱福贵也没客气,自顾自抄起吧台上的陶壶,给自己满满斟了杯温热的大麦茶,而后咕咚一口灌下,咂摸着嘴,一脸的回味。
“九娘,你说这人呐,是不是天生就骨头贱。”
付九娘手上的动作未停,此刻,她终于舍得抬起那双狭长的眼帘,懒懒地递过去一个风情万种的白眼。
“你倒是今儿个才知道?”
她话音刚落,那扇木门又被接二连三地推开了。
原本只闻风声的小酒馆,顷刻之间,便被涌入的人声与热气给填了个满满当当。
山东大汉石磊和林跃的嗓门最大,人还没坐稳当,便扯着嗓子嚷着要酒,那动静震得人耳朵嗡嗡作响。
金翎和杨文雅,两个地道的北京大妞,则挑了个临窗的雅座,凑在一块儿交头接耳,也不知在聊些什么要紧的私房话。
其余的人,也各自寻了相熟的伴儿,三三两两地,围坐在那几张零散的旧木桌旁。
唯有陈默,那个广东来的男人,依旧寻了个最不起眼的角落坐下,镜片后的那双眼睛,习惯性地扫过屋子里的每一个人。
这小酒馆里,从不放什么靡靡之乐,有的,便只是这嘈杂的人声。
嗡嗡的,如盛夏午后最焦躁的蝉鸣,搅得人心绪不宁。
朱福贵压根没理会付九娘的那个白眼,他清了清嗓子,自顾自地便抛出了一个话头。
他声音不高,可那分寸却拿捏得恰到好处,刚好能让这屋里所有竖着耳朵的人,都听个一清二楚。
“我跟你们说个理儿啊。”
他端着茶杯,在手里轻轻晃着,脸上是一副故作高深的模样。
“但凡那种号称千杯不倒的男人,只要碰上那个对眼的女人,嘿,一杯就倒。”
他刻意顿了顿,很是受用地瞧着所有人的目光,都齐刷刷地聚了过来。
“反过来,也一样。但凡那种沾酒就倒的女人,要是碰上个不对眼的男人,你信不信,她能千杯不倒。”
这话一出,酒馆里凭空静了一秒。
随后,东北来的杨文雅最先没忍住,“噗嗤”一声便笑了出来。
“我说朱哥,您这又是打哪儿听来的歪理邪说啊?”
“嘿,这可不是歪理!”
朱福贵当即脖子一梗,脸都涨红了。
“这是人生哲学!”
坐在他对面的林跃,那个五大三粗的山东汉子,突然猛地一拍大腿,桌上的酒杯都跟着惊跳了一下。
“这话我信!不过,俺得补充一句!”
他一把端起面前的扎啤杯,仰头就是一大口,白色的酒沫子沾了满嘴都是。
“昨天有个小妹儿问我,说是不是只要一个长得不赖的姑娘主动,你们男的就没一个能扛得住?”
他把酒杯重重往桌上一顿,发出“砰”的一声闷响。
“我说,那能吗!当然不是!”
他一脸的义正辞严,说得斩钉截铁。
众人正要点头,却见他嘿嘿一笑,露出一口白牙,眼里带着几分藏不住的狡黠。
“有时候,长得难看的,俺也不一定能控制住自己。”
“吁——!”
满屋子顿时响起了嫌弃的嘘声和此起彼伏的笑骂。
苏晓柔,那个文静的湖南妹子,脸颊上都泛起了一层红晕,低声啐了一句:“流氓。”
林跃却不以为耻,反以为荣,哈哈大笑起来。
“这叫实诚!”
这时,角落里,一直没怎么说话的北京大妞金翎,突然伸出修长的食指,在面前的木桌上,不轻不重地敲了三下。
叩,叩,叩。
那声音不大,却有一种奇异的穿透力,竟让这满屋子的嘈杂,瞬间便安静了下来。
所有的目光,齐刷刷地,全聚向了她。
她端起那杯红酒,送到唇边,只轻轻抿了一小口,眼神却锐利得如同一把刚刚出鞘的刀。
“男人那点儿花花肠子,有什么难猜的。”
她的声音清清冷冷,带着京片子特有的那股子干脆利落劲儿。
“我告诉你们,当一个男人同时爱上两个女人时,他到底更爱谁,压根儿不用去看他对谁更好。”
金翎的嘴角,缓缓勾起一抹讥诮的弧度,冷得彻骨。
“看谁,更不待见他,就完了。”
这话一出,满场死寂。
方才还大大咧咧的几个男人,包括林跃在内,脸上的表情都变得极不自然起来。
重庆来的龙瑾瑜,那个平日里骄傲得如一只开屏孔雀般的女人,此刻竟抚掌一笑,清脆的掌声在这片寂静之中,显得格外响亮。
“金姐这话,算是说到根儿上了!”
她扬起尖俏的下巴,目光如炬,毫不客气地扫过在场的每一个男人。
“我再给你们翻译翻译,掰开了,揉碎了说。”
“男人啊,不是喜欢素颜的女孩儿。”
她的声音又脆又亮,带着川渝女子那股子天生的泼辣劲儿。
“是喜欢——素——颜——也——漂——亮——的,懂了吗?”
她一字一顿,说得是斩钉截铁。
旁边的杨文雅听了,深以为然地点着头,用她那股东北大碴子味的普通话接茬道。
“可不是咋地。”
她重重叹了口气,一脸的过来人神情。
“也甭老说男人不喜欢女汉子,那纯属扯淡。”
“你瞅瞅,但凡是漂亮的女汉子,他们哪个不稀罕着呢!”
这一句句话,便如一记记无形的耳光,火辣辣地,扇在了屋里所有男人的脸上。
素来勤恳踏实的福建人石磊,下意识地挠了挠头,张了张嘴,却发现一个字都辩驳不出来。
颇有领导派头的上海男人林啸峰,端着酒杯,眼神里满是若有所思。
就连那个少数民族出身,一向鬼点子最多的侯天乐,此刻也只是咧着嘴,干巴巴地笑着,一言不发。
气氛,一时尴尬到了极点。
付九娘依旧倚在吧台后头,瞧着这群红男绿女的众生相,只是勾着唇角笑,不言语。
她又拿起一只干净的杯子,继续慢悠悠地擦拭。
这一场唇枪舌剑,于她而言,不过是一出有趣的下酒戏罢了。
最终,是那个一直缩在角落里的陈默,那个精于算计的广东人,慢悠悠地开了腔。
他的普通话里,裹着一股子怎么也洗不掉的粤语腔调,每个字都咬得很慢,却异常清晰。
“其实,你们说的,都对。”
他抬起手,用食指的指节,轻轻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。
“但是,你们说的,都只是过程,不是结果。”
他停顿了一下,似乎在脑中精确地组织着每一个字眼,每一个词。
“一个男人,在一段感情里,最怕的是什么?”
他缓缓抬起头,镜片后的那双眼睛里,闪烁着一种冷静到近乎残忍的光。
“最怕的,是掏心掏肺,又掏钱。”
他的声音很轻,却如同一记重锤,狠狠砸在了每个人的心口上。
“最后,却发现遇到的,是个潘金莲。”
「潘金莲」这三个字,便如一盆数九寒冬的冰水,兜头浇下。
整个酒馆的空气,瞬间凝固。
方才还热火朝天的气氛,骤然降至冰点。
所有人都沉默了。
女人们脸上的笑意尽数敛去,而男人们,则是一脸无法言说的复杂,眼神里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感同身受。
朱福贵端着茶杯,忘了喝。
林跃脸上的嬉皮笑脸也收得一干二净,罕见地锁紧了眉头。
金翎那根敲击桌面的手指,也停在了半空之中,再没了动静。
陈默这一句话,便如一把锋利至极的手术刀,精准无比地剖开了男女关系之中,最血淋淋、最现实的那一面。
所有虚伪的浪漫与试探,都被剥得干干净净,只剩下赤裸裸的利害与算计。
不知过了多久,久到空气都变得粘稠。
一直安安静静坐在那里,如一个局外人般的四川姑娘沈思敏,突然放下了手中的茶杯。
杯底与桌面相触,发出一声极轻的“叩”。
这一声轻响,却成了打破这片死寂的唯一声音。
她抬起头,那双总是波澜不惊的眸子里,此刻竟闪烁着一种洞穿人心的锐利。
她看着满屋子神色各异的男男女女,声音不大,却清晰地钻进了每个人的耳朵里。
“那你们说……”
“对一个女人而言,是身边那个男人骗了她一辈子,更可怕……”
她唇角逸出一丝极淡的笑意,轻飘飘地,抛出了后半句话。
“还是那个男人,把所有事情最残酷的真相,一字不漏地都告诉了她,更可怕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