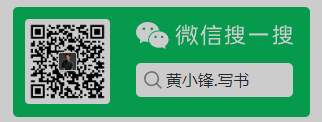灯光是昏黄的。
将那张不知用了多少年的老旧木吧台,浸染出一层温润油光。
空气里头,是麦芽发酵后的醇香,里头还夹着一股子老木头味儿。
朱福贵端起杯子,粗壮的脖颈一仰,咕咚咕咚便是一大口冰啤灌进了喉咙。
那股子透骨的凉意,便是一道冰线,直直地刺入胸腹,激得他浑身一个舒爽的激灵。
“嗝……”
一声石破天惊的饱嗝,毫无征兆地,便撕破了酒馆里那点低缓的音乐。
“我说老朱,你这是喝啤酒呢,还是活吞了个蛤蟆?”
坐在对面的东北姑娘杨文雅,当即伸出两根涂着蔻丹的指头,死死捏住了自个儿的鼻子,满脸皆是毫不掩饰的嫌弃。
她那两条新潮的野生眉紧紧蹙起,几乎要拧成一个疙瘩,透着一股子随时准备“削他”的彪悍劲儿。
朱福贵嘿嘿一笑,毫不在意地露出了两排被烟熏得微黄的牙。
“这叫生活的交响乐,懂不懂?你们这些小年轻,就是没得情调。”
他晃了晃自己圆滚滚的啤酒肚,舒坦地靠进椅背,脸上是一种全然的陶醉。
这时,一直安静望着窗外夜色的沈思敏突然开了口。
她的声音不大,却清凌凌的,如一颗小石子,轻轻投入了这片微醺的空气里。
“你们还记不记得,小时候摔一跤,第一反应是什么?”
此问没头没尾,显得有些突兀。
众人皆是一愣。
脑子转得最快的侯天乐眼珠子一转,当即抢着开了腔:“嘿,那还用问么您?”
“肯定是先拿眼角余光扫一圈,瞅我妈在不在旁边!”
“要在,那得赶紧扯开嗓子嚎,声儿越大越好,最好带点颤音。”
“要不在?那还哭个屁!拍拍土,自个儿麻溜爬起来呗,难不成哭给电线杆子看啊?”
他这话一出,瞬间引来一片哄堂大笑。
“哎呀妈呀,可不是咋地!”
杨文雅一巴掌重重拍在自己大腿上,嗓门瞬间就掀了顶棚。
“我小时候就这德行!我妈要是在跟前,我能从街头哭到街尾,眼泪鼻涕糊得满脸都是,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让人把腿打折了!她要不在,我便是磕掉半颗门牙,也能自个儿面不改色地给它按回去!”
勤恳老实的福建人石磊憨厚地笑了笑,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后脑勺。
“好像……好像是真的。有大人在,就感觉自己格外委屈,疼得也厉害些。”
“这不是委屈。”
一向精于计算的广东人陈默,慢条斯理地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。
“呢个,叫成本效益分析。”
他伸出一根食指,有条不紊地在空中点了点。
“当住大人面喊,收益是:有机会得到糖果、安慰,甚至唔使做功课,回报率好高。”
“自己一个喊,成本是:除咗浪费口水同力气,乜都冇。”
“冇回报嘅事,傻仔先做。”
他一番条理清晰的歪理邪说,竟说得众人哑口无言,可仔细一咂摸,还真就是这么个理儿。
北京大妞金翎撇了撇嘴,端起酒杯抿了一口。
“得,陈总,您这算盘珠子都快崩到我们脑门上了。什么事儿到了您这儿,都得先扒拉一遍算盘。”
陈默只是耸耸肩,镜片后的眼睛里明明白白写着“我讲的都是事实”。
“但你们发现没?”
一直没怎么说话的苏晓柔,用她那特有的温软嗓音,将话题又轻轻地拉了回来。
她搅动着杯中的柠檬水,冰块与杯壁碰撞,叮叮当当,发出清脆的微响。
她的眼神有些飘忽,落在了窗外那片无边无际的夜色里。
“长大以后,这事儿就彻底反过来了。”
此言一出,方才还喧嚣热闹的小酒馆,骤然一静。
那些笑声与吵闹,便如退潮般,无声无息地散了,沉淀下来,只余下空气中无声的思索。
每个人的脸上,都浮现出一种混杂着苦涩与了然的神情。
是啊。
反过来了。
全都反过来了。
苏晓柔的声音还在继续,轻得如一声叹息,飘散在空气里。
“现在遇到不开心的事,第一反应也是先看周围有没有人。”
“有,就得赶紧爬起来,擦干净脸上的泥,笑得比谁都灿烂,比谁都若无其事。”
“只有在四下无人的时候,才敢找个角落,自己抱住自己,跟自己哭一场。”
“我记得我小时候,俺娘有口仙气。”
精力充沛的山东大汉林跃,声音难得地低沉下来。
他那蒲扇般的大手,正无意识地摩挲着冰凉的啤酒杯壁,杯壁上凝结的水珠濡湿了他的指尖,带来一片凉意。
“不管磕哪儿碰哪儿,只要俺娘对着伤口‘呼呼’吹两下,嘿,立马就不疼了。比什么红药水紫药水都管用。”
“对对对!”
重庆妹子龙瑾瑜立刻接上了话,她的性子如沸腾的火锅般火辣,此刻眼眶里却闪着一层晶莹的水光。
“我妈也是!我到现在都想不通是啥子原理,那口气简直就是神丹妙药!”
“那叫安慰剂效应,懂吗您内?”
金翎又开始她的“科普时间”,“纯纯的心理作用。因为你信她,潜意识里就觉得不疼了,大脑分泌内啡肽了呗。”
“去你的心理作用!”
龙瑾瑜白了她一眼,眼圈却红了。
“反正我不管,那就是仙气!你们这些没得感情的科学家,解释不了我们母女之间的玄学!”
吧台边,老板娘付九娘倚着柜台,静静听着他们的争论,嘴角始终噙着一抹淡淡的笑意。
她没说话,只是默不作声地拿起酒瓶,给金翎的杯子又添了些酒。
“小时候啊,总觉得天黑得太快。”
一直很有领导派头的上海人林啸峰,此刻也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他松了松领带的温莎结,整个人都陷进了宽大的椅子里,显出几分平日里难见的疲惫。
“总盼着白天能再长一点,再长一点,这样就能在外面多疯玩一会儿。”
“如今呢,倒是反过来了,天天盼着天赶紧黑,盼着这夜晚能再长一些,再长一些。”
“因为只有当夜幕降临,才感觉压在身上一整天的担子……总算是能暂时卸下了。”
他的话,如一块沉甸甸的石头,不偏不倚地砸进了在场每个人的心湖里,激起一圈又一圈无声的涟漪。
白天的时间,属于工作,属于客户,属于老板,属于家庭里的鸡毛蒜皮。
只有这黑夜里偷来的一点点辰光,才真正属于自己。
“以前也搞不懂。”
责任感很强的广州人赵忠信,突然哼起了一句老歌的调子。
“‘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,让它牵引你的梦’……小时候听罗大佑唱这个,就觉得很奇怪,为啥非要让青春吹动长发?短发不行吗?寸头不行吗?难道我们男的就不配有青春?”
他这个问题,让沉闷的气氛瞬间被打破,大家都乐了。
侯天乐笑得最夸张,身子一仰,差点从高脚凳上滑下去。
“哈哈哈,老赵,你这个问题问得好!特别有深度!直击灵魂!”
赵忠信却一脸认真。
“我是真的想了很久。”
“我现在明白了。”
一直为发际线忧心忡忡的石磊,此刻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头顶,神情悲壮,如一个即将奔赴沙场的勇士。
“因为人到中年,就秃了。”
“别说长发了,到时候连给青春一个吹动机会的头发,都没了。”
“噗——”
朱福贵刚喝进嘴的一大口酒,没能忍住,当场就喷了出来,化作一道精准的抛物线,不偏不倚,尽数洒在了对面陈默的脸上。
陈默的脸,瞬间黑如锅底。
他僵硬地摘下眼镜,从纸巾盒里抽出纸,一点,一点,极慢极慢地擦拭着镜片上的酒渍与泡沫。
那眼神,隔着朦胧的镜片,都几乎能将朱福贵凌迟处死。
“朱福贵,你搞咩啊!”
一声压抑着火山爆发般怒火的粤语低吼,彻底点燃了全场。
整个小酒馆,瞬间爆发出惊天动地的笑声。
杨文雅笑得眼泪直流,一边捶着桌子一边喊:“哎呀妈呀,石磊你可真是个人才!神总结!我给你点三十二个赞!”
林跃笑得满脸通红,蒲扇大的手掌重重拍在石磊的肩膀上,震得他一晃一晃的。
“兄弟!扎心了!俺也快了!”
连一向冷静理性的沈思敏,都忍不住笑弯了腰,肩膀微微地耸动着。
这群人,前一秒还在伤春悲秋,感慨人生,后一秒就因为一个秃头的笑话,笑得前仰后合,毫无形象可言。
付九娘看着这群笑得东倒西歪的家伙,也终于忍不住,轻笑出了声。
她拿起一块干净的毛巾,递给手忙脚乱的陈默,而后走到了酒馆中央。
她轻轻清了清嗓子。
喧闹的场子瞬间安静下来,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到了她身上。
付九娘的目光,缓缓扫过每一个人的脸,温和而有力量。
她的声音,带着一种被岁月淘洗过的独特磁性,不轻不重,却清晰地落入每个人的耳中。
“我们都长大了。”
她顿了顿,眼神里有笑意,也有几分过来人的通透。
“所以啊,开心的时候,就学学老朱,尽情地笑,笑得打嗝放屁都无妨。”
朱福贵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后脑勺,嘿嘿地笑着,不敢言语。
“伤心的时候,也别学你们现在这般,非要寻个无人角落。”
她的视线落在苏晓柔身上,带着一丝暖意。
“想哭,就痛痛快快哭一场,哭得天翻地覆也无所谓。”
“这些情绪,笑也好,哭也罢,都是活着的证明。”
付九娘端起自己的酒杯,朝着众人举了举。
“千万,别憋在心里。”
话音落下,满座皆静。
他们看着付九娘,看着彼此眼中映出的、那个同样疲惫而又努力笑着的自己,然后,不约而同地,缓缓举起了手中的酒杯。
“叮——”
清脆的碰杯声,在小酒馆里轻轻回荡,悠长。
这一刻,没有老板与员工,没有本地人与外地人。
只有一群,在这座巨大的城市里努力活着,会笑,会哭,会痛,也会笨拙地互相取暖的普通人。
突然。
“吱呀——”
小酒馆那扇颇有些年头的木门,应声而开。
一道身影,逆着光,轮廓被勾勒得模糊,就这么静静地立在了门口。
满屋的谈笑声,在此刻戛然而止。
所有人的目光,齐刷刷地,尽数投向了门口那道模糊而又神秘的轮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