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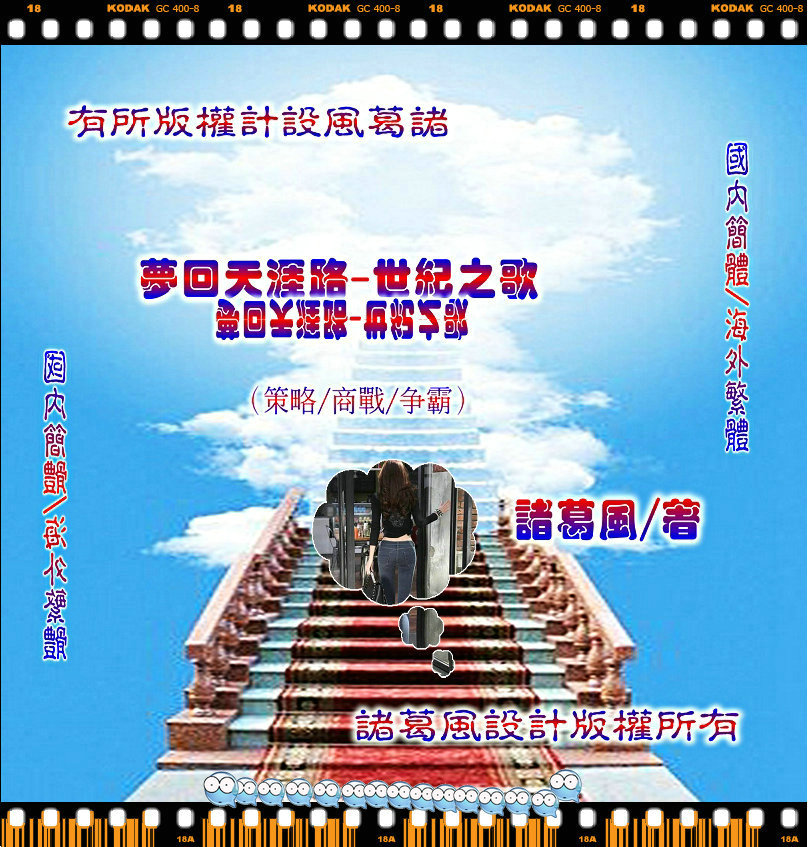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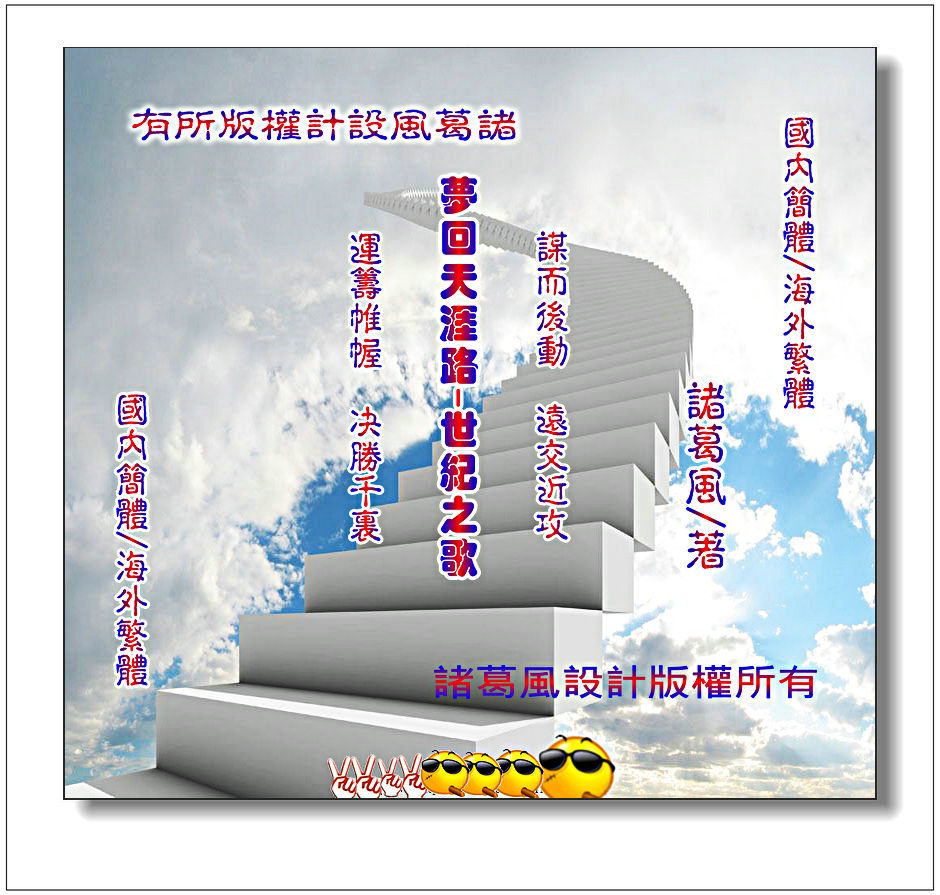
第七章.反腐倡廉
蒋曼云眼皮子刚跳了两哈,就晓得公司里要出个么蛾子。她在茶水间杵着,听见两个科员正扯皮,一个说 “市场部那班子人撮虾子撮得飞起,怕是要把公司撮成漏勺”,另一个接茬 “项目部的方案?我看是用脚底板写的,还不如厕所里的卷纸有用”。这些裹筋的话像长江里的暗流,搅得她心里头七上八下 —— 毕竟黄金海岸正跟 “海南天地” 啃那个 XX 策划案,要是合同黄了,董事长怕是要把办公室的鱼缸都掀了,说不定祖坟真得冒青烟。
夜里十点,她猫着腰摸到董事长办公室。老头子正捧着本《三国演义》,老花镜滑到鼻尖上,活像个偷拆学生信件的私塾先生。“Uncle,您还在研究借东风啊?” 她故意把武汉话里的 “叔叔” 念得拐了十八道弯,“再不管哈子,市场部跟项目部怕是要在会议室打码头,到时候桌椅板凳都得见血。”
董事长 “啪” 地把书合上,镜片后的眼睛突然放出精光,活像归元寺里的琉璃灯:“小曼你莫慌,明早开会我自有计较。” 他从抽屉摸出个铁盒,里头装着汉口精武鸭脖,油光锃亮的,“来一根?这味道,比杨兴安那班子人玩的套路正多了,起码不塞牙。”
次日会议室里,空调冷得像腊月的汉江,冻得人只想把脖子缩进衣领里。杨兴安穿得像个刚从婚车上跳下来的新郎倌,领带打得比他的良心还周正,皮鞋亮得能照见天花板上的吊扇。董事长敲了敲保温杯,开口就是句武汉老话:“各位,江湖不是打打杀杀,是人情世故 —— 这话还是我爷爷跟我讲的,他当年在六渡桥卖热干面,就靠这道理混到了三套房。” 他端起杯子喝了口茉莉花茶,茶叶在水里翻来翻去,“我看咱们公司就像长江里的货船,要是有人在底舱凿洞,船沉了哪个都跑不脱,到时候连汉阳门的救生圈都救不了你们。”
杨兴安的脸瞬间白得像户部巷的豆皮,还是没加酱料的那种。他想起上周在员工食堂放的厥词:“蒋曼云那丫头片子懂个莫斯?她那方案拿去擦屁股都嫌硬,怕是石头做的。” 现在这话像回锅的藕汤,糊在喉咙里咽不下去,烫得他直翻白眼。
散会后,蒋曼云故意堵在杨兴安办公室门口,倚着门框像尊笑面佛。“杨主管,听说您最近在研究‘鹓雏与猫头鹰’的故事?” 她笑得像昙华林的雕花窗,弯弯绕绕全是心眼,“不过我更想听您讲讲,市场部的‘撮虾子’文化 —— 是不是还得配着户部巷的油饼包烧卖才够味?” 杨兴安的冷汗顺着发梢往下滴,活像被戳破的汤包,连衬衫都洇出了深色的印子。
三天后,“海南天地” 的肖英打来电话,声音里带着热干面的芝麻酱味。“陈总啊,您这方案写得比户部巷的热干面还地道,芝麻酱都拌得匀匀的。” 他突然压低声音,像怕被隔壁桌听见,“不过张强那边放出话来,说要跟您拼个鱼死网破,怕是要学老通城的豆皮,非把对方压成薄脆不可。” 陈军望着窗外的长江大桥,烟头在烟灰缸里明明灭灭,活像江面的航标灯:“肖兄,麻烦您带个话 —— 长江水养不了两家船,该让的时候就得让,莫学那些在吉庆街扯皮的醉汉,非要闹到巡捕房才甘心。”
夜里,蒋曼云在江汉关博物馆外头散步,江风裹着轮渡的汽笛声,把她的头发吹得像乱蓬蓬的芦苇。手机突然震动,是董事长发来的消息:“明天宣布你升任总经理助理。记住,莫学杨兴安那班子人玩虚的,要像长江水一样实在,该涨潮时涨潮,该退潮时退潮,别学那些在江滩放风筝的,线断了就只能望着天上发呆。”
她望着对岸的灯火,突然笑出了声,惊飞了江边的夜鹭。这汉口的夜啊,永远比武昌的月亮热闹,就像她兜里那包周黑鸭,表面甜丝丝的,里头辣得人心慌,偏生越辣越想吃。这江湖啊,还得接着混下去,总不能学那些在汉正街迷路的外地人,哭着喊着要回家。
汉江潮涌接武昌,汉口繁华自古扬。
公司楼里风波起,曼云心惊觉不祥。
茶水间内人私语,市场项目互攻讦。
撮虾子与脚底板,言语如刀割肝肠。
合同若黄祸非小,董事长怒恐掀缸。
夜探办公室深处,老总灯下读三国。
眼镜滑鼻似学究,曼云巧语逗翁乐。
“借东风事且慢论,部门将战如楚河。”
董事长言自有计,铁盒鸭脖递过来。
“此味胜彼虚套路,嚼得江湖真意来。”
次日会议冷气冽,兴安衣鲜如嫁郎。
领带周正良心伪,董事长言喻深长。
“江湖非是打杀场,人情世故为大纲。
公司似船长江里,凿洞同沉莫慌张。”
兴安面白如豆皮,昔日狂言梗喉间。
会后曼云拦去路,笑问撮虾子秘传。
汗出如浆破汤包,主管窘迫无一言。
三日海南传消息,肖英赞案胜热干。
张强放言拼鱼死,陈军稳坐望江滩。
“长江难容双舟并,该让之时莫强顽。”
夜步江汉关前月,江风汽笛乱鬓鬟。
忽得老总升迁令,嘱语谆谆记心间。
“莫学兴安玩虚套,要似江水本真然。”
对岸灯火映笑靥,周黑鸭辣藏甘甜。
汉口夜色胜武昌,江湖路远续新篇。
潮起潮落随波去,且将俗事付云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