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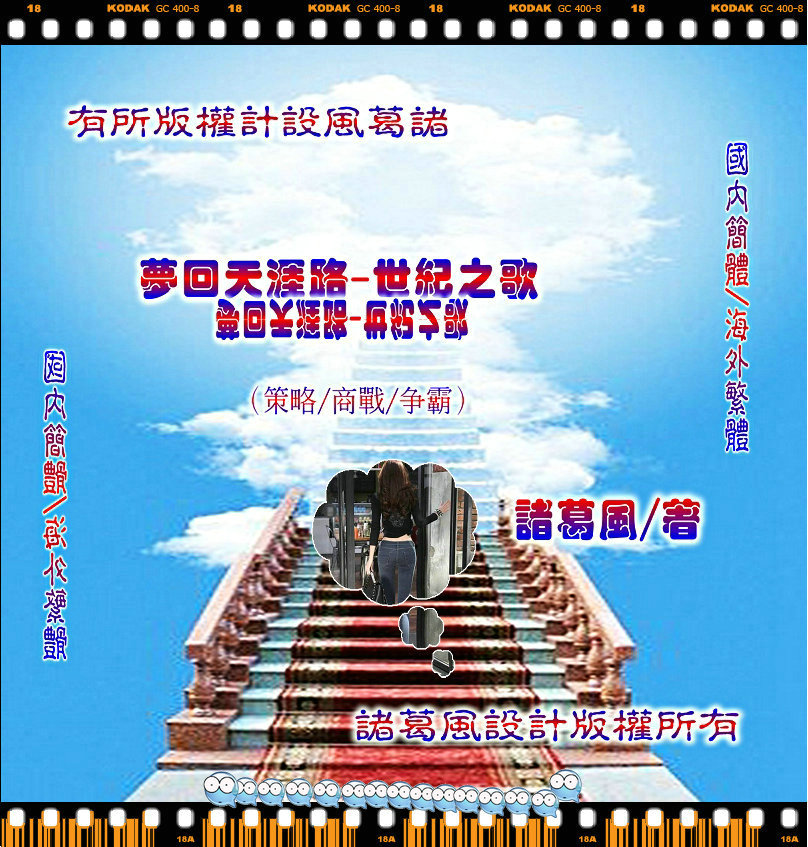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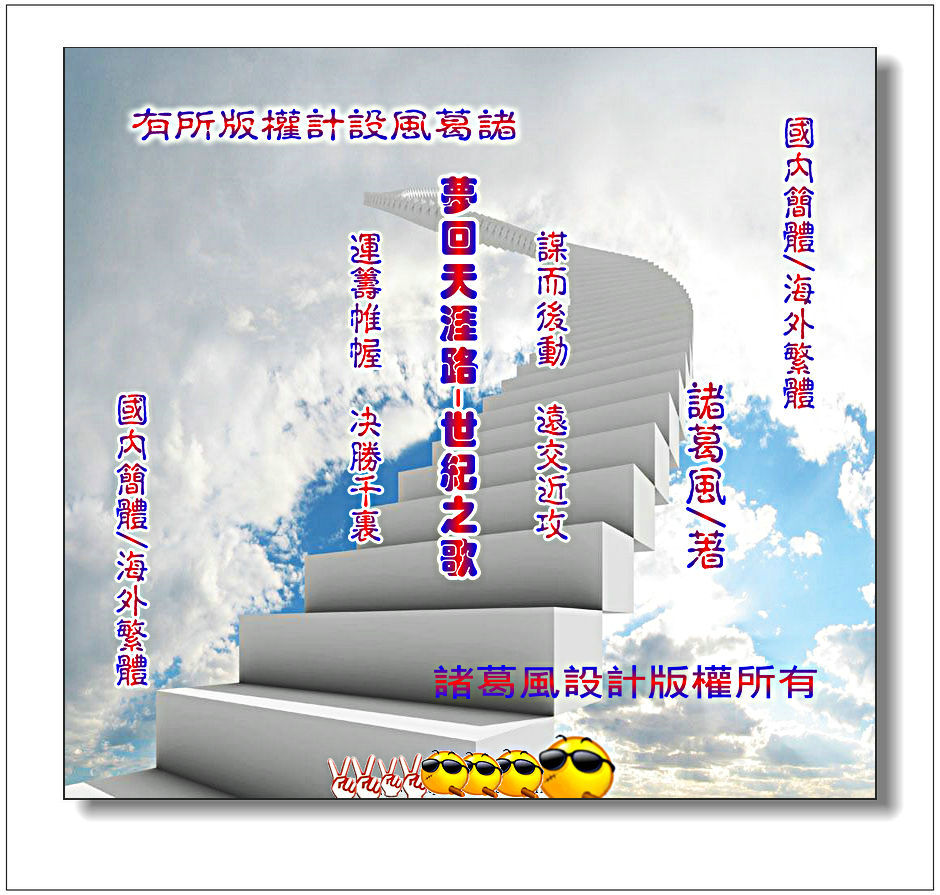
第四十七章.作壁上观
“是的撒,” 陈军从文件夹里薅出个 U 盘,手指头在上面转得跟玩金箍棒似的,“1985 年开放那天,周导在黄鹤楼顶逮住设计师向欣然,老东西在录音里嚼:‘黄鹤楼重建,不是拿个模子倒石膏,是让这千年的老骨头,在新时代活出点新板眼。’”
林小婉的红指甲在桌面上敲得跟打快板似的,忽然就跟遭了雷劈似的 —— 自己居然栽在最瞧不上的东西上:那点人味儿。老照片里工人师傅咧嘴笑的褶子,录音里带颤的气口,比她那些花里胡哨的光影魔术管用多了,简直像巷子里的热干面,看着糙,吃着暖心窝子。
招标会散场时,夕阳把黄鹤楼裹得跟块虎皮蛋糕似的。陈军戳在景区门口,盯着玻璃柜里的黄鹤楼雪糕直乐 —— 奶油正顺着楼檐往下淌,跟个没穿尿不湿的伢似的,在暮色里哭得一塌糊涂。林小婉的高跟鞋声从后头飘过来,没了先前的炸毛劲儿:“当年在昙华林,你总嚼我画的黄鹤楼太假,跟百货公司橱窗里的糖人似的。现在看来,你个板马还真说对了。”
他转过身,瞅见她摘了墨镜,眼尾的细纹里盛着落日的碎金,倒比平时顺眼多了:“我爹走之前总说,我跟我妈一个德性,死抠那些线条框框,倒把框框里的人影儿给忘干净了。”
江风裹着潮气扑过来,陈军摸了摸裤兜,想起老娘临终塞给他的奥特曼挂件,现在正躺在办公桌抽屉里积灰。“我九岁在江汉路丢了个书包,后来老娘在夜市上又扯了个一模一样的。她跟我说,有些东西丢了能捡回来,有些东西要是飞了,那就真成黄鹤了 —— 一克不复返。”
手机震得跟揣了个跳跳糖似的,曲俊发来条消息:“中了!王建国刚打电话,联创想掺和纪录片,说要学周导那套,玩点土味的。”
文创店的电子屏正放着新世纪传媒的广告,声音大得跟吵架似的:“每个时代都在给黄鹤楼写传记,我们就是那个翻话本的。” 陈军望着屏幕上老工匠的手跟设计师的手在虚拟斗拱上握一块儿,突然跟通了电似的 —— 所谓传承,哪是跟时光对着干?分明是把日子捧在手心,让它慢慢流,跟长江水似的,绕着弯儿也得往前奔。
回武昌的车上,曲俊拧开香槟,泡沫喷得跟喷泉似的:“下一站,汉口租界。那帮老房子正等着翻新,林小婉的公司也在里头搅和。”
陈军望着长江大桥上的车流,想起下午在黄鹤楼顶瞅见的景儿 —— 两江交汇的浪头吵吵嚷嚷的,却都朝着一个方向跑。他心里跟明镜似的,跟林小婉的架还得接着吵,但更要紧的是,俩人为这座城的记性忙活,不过是一个爱啃热干面,一个爱喝蛋酒,口味不同,心都是热的。
…… 深更半夜的汉街写字楼,陈军对着电脑整理租界资料,突然弹出来个匿名邮件,跟鬼敲门似的。点开一看,是段老视频:1998 年抗洪那会儿,周明义在江汉关楼顶上扛着摄像机,王建国跟条狗似的趴在地上,镜头里浑黄的江水正漫过沿江大道的路牌,跟饿狼吞肉似的。视频末尾,周明义转过来对着镜头笑,脸上的泥点子跟麻子似的:“等水退了,得让后人晓得,这城的骨头有多硬,都藏在被洪水啃过的砖缝里。”
他盯着屏幕上那定格的笑脸,突然想起王建国办公室的台历,红圈标着 “周丽芳忌日”,旁边歪歪扭扭写着:“今儿去江滩放风筝了,你说得对,砖里头都藏着故事,跟老汉口的码头上,每块石头都记得起吊过多少洋行的箱子。”
键盘声在空办公室里跳着踢踏舞,陈军敲起租界项目的策划案,标题就叫《砖缝里的光阴》。他心里门儿清,明天得跟曲俊去汉口同兴里,见个在老洋房里住了七十年的翻译家。老头的笔记本里记着 1949 年解放军进租界时,在门楣上敲的钢印编号,跟给老房子盖了个出生证明似的。
凌晨两点的键盘声跟蚊子哼似的,陈军盯着周明义的笑脸,视频里的洪水好像还在眼珠子上晃。邮件发送时间是 23:47,发件人地址跟乱码似的,倒像 1998 年抗洪时那些没留名的慰问信,字歪歪扭扭的,心却是滚烫的。他把截图存进文件夹,文件名备注:江汉关顶的泥菩萨笑了。
窗外的汉街早没了霓虹灯的疯劲儿,写字楼玻璃上沾着几颗星星,跟没擦干净的鼻涕似的。陈军揉了揉酸脖子,抽屉里的奥特曼挂件在台灯下泛着哑光,塑料壳上的划痕里卡着二十年前的太阳。老娘临终的话突然在耳边炸响:“有些东西丢了能找回来,有些东西要是没了,那就真成了汉口老通城的豆皮 —— 想吃也吃不上了。” 他摸出手机给曲俊发消息:明早九点,同兴里 32 号,带上扫描仪,别跟个苕似的忘了。
梧桐树的影子在鄱阳街上跳着迪斯科。曲俊的黑 SUV 停在同兴里巷口时,陈军正对着手机地图犯迷糊 —— 这片 1930 年代的西式里弄,跟被冻住的棋盘似的,红砖墙爬满爬山虎,跟穿了件绿毛衣。
“哎,你今儿穿得跟中学班主任似的,要去训话?” 曲俊递过冰镇矿泉水,看着他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浅灰亚麻衬衫直乐。陈军扯了扯领口,指尖摸到衣摆处老娘手缝的线,跟摸到乡愁似的:“张教授说他爹的笔记本娇气,得穿得让老人家看着顺眼,别跟个搞传销的似的。”
32 号的铁门虚掩着,门楣上的铜牌号磨得跟块旧银元似的,就门拱中央的钢印 “汉租字第 47 号” 还精神,凹痕里积的灰够炒盘菜了。推门时 “吱呀” 一声,惊飞了檐角的麻雀,满院的紫藤花跟瀑布似的砸下来,在青石板上泼了摊紫墨水。
“是新世纪传媒的先生吧?” 拄拐杖的老头从藤椅上站起来,藏青色中山装洗得跟纸似的,胸前口袋露半截钢笔帽,跟别了根银簪子。“我是张墨林,我爹张叔平 1946 年盘下这房子。” 他的声音跟泡了水的旧报纸似的,却带着股子说书先生的调门。
会客厅的摆设跟 1980 年代冻住了似的:雕花五斗柜上摆着上海牌座钟,玻璃罩里的铁皮青蛙还保持着蹦跶的姿势,跟被施了定身法。张墨林颤巍巍捧出红绸布包的笔记本,纸页黄得跟深秋的银杏叶,头行小楷写着 “租界区房产接管纪实”,笔锋硬得跟汉正街的扁担似的。
“我爹当时在江汉关当翻译,解放军进城那天,他跟着接收小组挨家挨户登记。” 老头戴上圆框老花镜,手指头划过 1949 年 5 月 16 日那页,“这页记的是同兴里 32 号,原房主是英国怡和洋行的买办,门楣钢印是军管会的同志当场敲的,编号规则是‘汉口租界’首字母加序号,跟给新生儿上户口似的。”
陈军的扫描仪 “嗡嗡” 哼着,曲俊凑过来看热闹,发现笔记本里夹着张泛黄照片:三个穿军装的年轻伢站在门拱下,中间那个举着铁锤,钢印在太阳底下闪着冷光,跟块新打出来的银元。照片背面用蓝黑钢笔写着:李建国、王建军、周明义,1949 年 5 月汉口。字歪歪扭扭的,倒有股子兵味儿。
“周明义?” 陈军的手指头突然僵住,这名字在黄鹤楼项目里跟幽灵似的,这会儿居然以年轻战士的模样,从老照片里钻出来了。张墨林点点头:“周同志当时是军管会文工团的摄影师,每敲个钢印都要拍照存档,说这些编号是新时代给老房子盖的胎记,跟娘胎里带出来的似的。”
老头从五斗柜深处翻出个铁皮盒,里面码着三十几张黑白照片,记着 1950 年代到 1980 年代的同兴里:穿布拉吉的姑娘在紫藤花下看书,戴红袖章的红卫兵在门楣上刷标语,改革开放后第一家裁缝铺的霓虹灯把里弄照得跟戏台似的。
“您看这张,” 张墨林指着 1983 年的照片,门拱下方新砌了堵砖墙,“那年我结婚要婚房,爹找人用长江边捡的抗洪砖砌了这墙。” 砖块表面的水痕跟地图似的,有些砖上还留着模糊的编号,像老天爷刻的密码。
曲俊突然指着照片里墙根的阴影:“这些砖是不是跟江汉关抗洪视频里的一个德性?” 陈军凑近了瞅,潮湿的砖缝里长的青苔,竟跟视频里周明义拍的路牌水痕有点像,跟失散多年的兄弟似的。老头浑浊的眼睛亮了:“那年洪水退了,沿江大道清出上万块旧砖,爹说这些砖喝饱了长江水,该让它们接着护着这方水土,跟老祖宗留下的守护神似的。”
快到中午时,张墨林非要留饭,铝制饭盒里装着排骨藕汤,藕块上还带着洪湖的泥腥气,跟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。老头说 1962 年冬天,周明义带摄制组来拍里弄生活,在他家借住三天,临走送了本《摄影构图教程》,扉页上写着 “让老房子自己说话,别总替它们瞎嚷嚷”。字如其人,硬邦邦的。
“上周有个戴墨镜的女的来看房子,” 老头突然压低声音,跟说悄悄话似的,“说要把这儿改成网红清茶馆,还要把那堵墙敲了做玻璃橱窗,跟把老祖宗的骨头挖出来展览似的。” 陈军和曲俊对视一眼,林小婉那副墨镜在太阳底下的反光,跟刀子似的突然闪进脑子。
吃完饭告辞时,张墨林往陈军手里塞了个牛皮纸袋:“周同志当年留给我爹的胶卷,前几年翻老屋时在地板缝里摸出来的,冲洗出来全是 1949 年敲钢印的事儿。” 纸袋上的封条还留着 1952 年的军管会公章,油墨早渗进纸纹里,跟长在肉里的痣似的。
回程的车上,曲俊专心开车,陈军翻着扫描仪里的笔记本,钢印编号在屏幕上投下深浅不一的影子,跟老汉口的里分巷子似的。翻到 1954 年的记录,一段字突然跳出来打眼:“今日帮周同志冲胶卷,发现 32 号门楣钢印照片里,砖缝里卡着片梧桐叶,准是敲印时飘进去的,跟老天爷盖的章似的。”
他忽然想起黄鹤楼文创店的雪糕,融化的奶油轨迹多像老砖上的水痕,跟时光流的泪似的。打开牛皮纸袋里的照片,1949 年 5 月的阳光穿过梧桐叶,在刚敲好的钢印上撒了把碎金子,叶片的锯齿边儿跟钢印凹痕严丝合缝,像时光打的双重结。
回到汉街写字楼时,暮色给玻璃幕墙镀了层金红,跟武汉人爱喝的蛋酒一个颜色。陈军打开电脑,新建的策划案《砖缝里的光阴》在屏幕上闪,跟等着开讲的故事。他先插了张墨林笔记本里的 1949 年照片,备注栏写:钢印不是终点站,是另一段故事的检票口。
邮箱 “叮” 地响了,匿名发件人又来信,这次是段 1954 年的录音,周明义的黄陂口音跟打雷似的:“汉口的老房子啊,每块砖都长着嘴呢,砖缝里藏着长江的涛声,藏着梧桐树的年轮,藏着敲钢印小伙子的汗味儿,跟腌在坛子里的酸豆角似的,越久越有味道。” 背景里隐约有砖刀敲墙的叮当声,跟在打节拍。
他盯着桌上的奥特曼挂件,突然懂了老娘说的 “找不回来的东西”—— 不是具体的物件,是物件身上带的时光味儿。就像黄鹤楼的斗拱、租界区的钢印,真正勾人的从来不是建筑本身,是建筑里淌着的人影儿,跟热干面里的芝麻酱似的,看不见摸不着,却少不得。
键盘声又响起来,陈军在策划案结尾敲:“当游客摸老砖上的钢印,得让 1949 年敲印战士的指纹,跟 2015 年游客的指纹在数字空间握个手。砖缝里的光阴不是标本,是条活水河,我们都是撑船的,把过去渡到将来。”
窗外的汉街亮起灯,跟打翻了的珠宝盒似的。陈军不知道明天跟林小婉又要吵成啥样,但他心里有数,等《砖缝里的光阴》投到租界老洋房的穹顶,那些被时光锁在砖缝里的故事,准会在数字光影里伸个懒腰,变成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桥。就像长江水,吵吵嚷嚷的,却始终朝着一个方向奔,有些东西,经得住时光的搓揉,才能露出最实在的模样,跟武汉人的心似的,看着糙,热得很。
凌晨五点的汉街写字楼像座透明灯塔,陈军桌上的台灯在玻璃上投出影子,跟个守夜人似的。他对着策划案里的 “钢印时光机” 示意图发呆,笔尖在周明义 1949 年的照片复印件上划了道浅痕 —— 照片里年轻战士举着的铁锤,木柄纹路竟跟家里旧工具箱里爹的榫头锤一个样,跟爷俩似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