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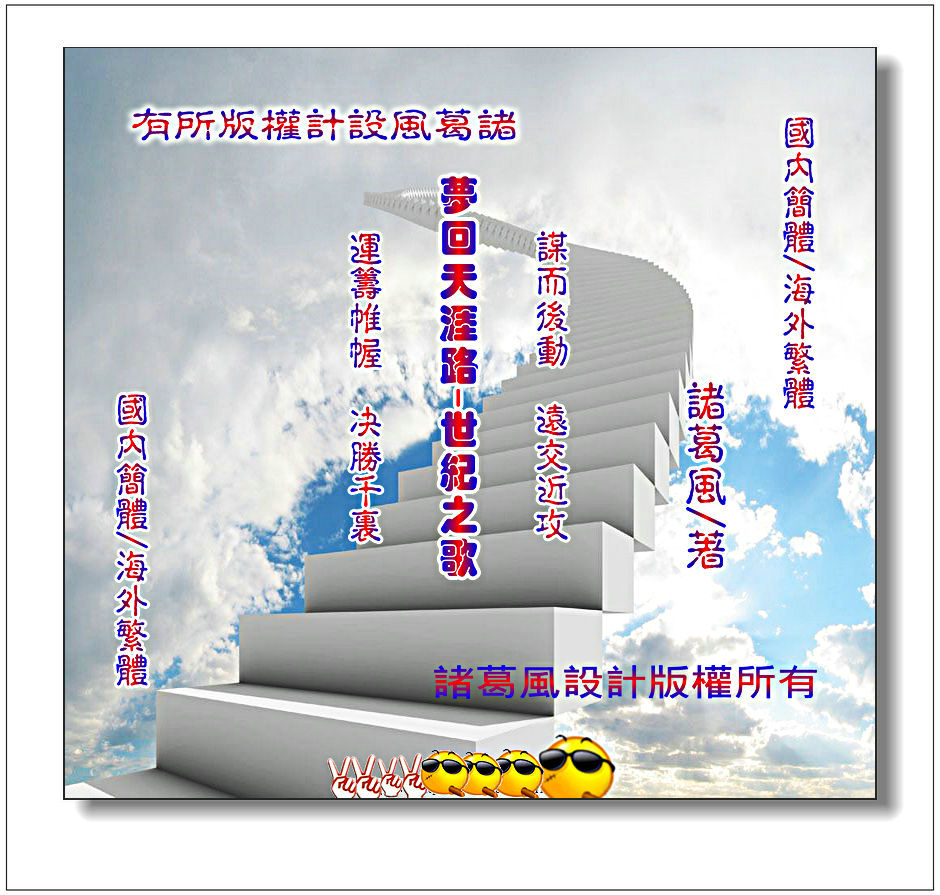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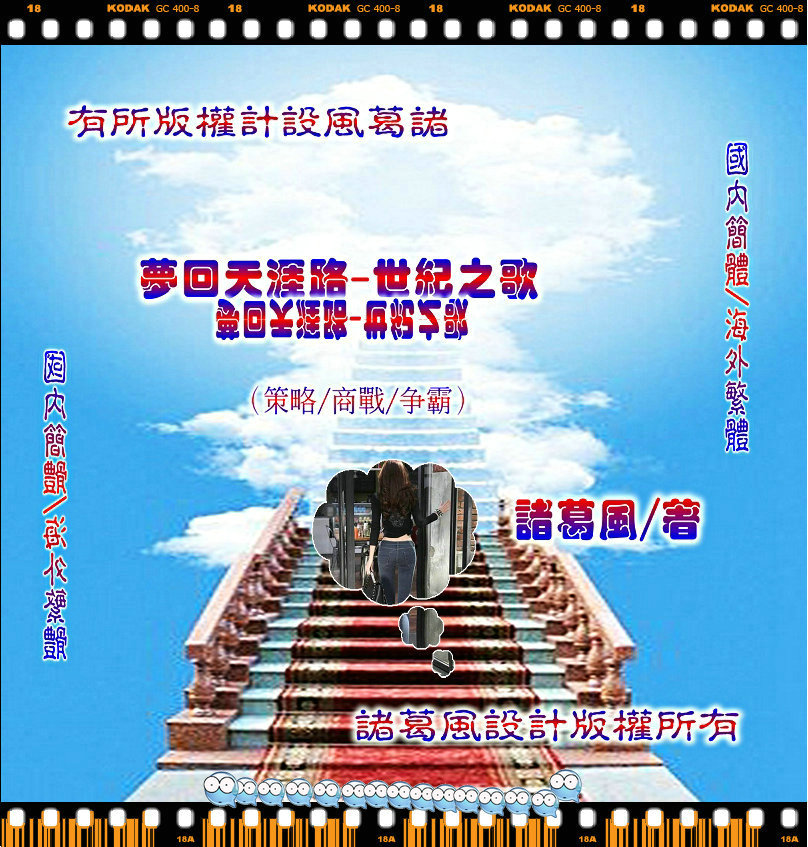
第一百二三章.先发制人
汉江潮卷暮云沉。
角声吟,刃光森。
十里长街,商战隐刀林。
昨日金樽同逐利,
今转瞬,起狼心。
残灯碎瓦溅血痕。
恨难禁,怒相侵。
宿怨新仇,拼杀撼城根。
谁记东坡诗酒意,
风过处,只余尘。
汉江的潮头卷着暮云下沉时,角声在暮色里长出锈迹。那些藏在霓虹灯影里的刀刃,正把十里长街雕成座密不透风的刀林。昨日碰杯时溅出的酒花还凝在杯沿,今天就有人把狼心掏出来,挂在楚河汉街的牌坊上晾晒。
陈军将文件拍在茶几上的力道,震得玻璃烟灰缸跳起了踢踏舞。"你以为这能要挟曲总?" 他冷笑时,嘴角的疤痕像条苏醒的蜈蚣,"这上面的日期,你老子还在牢里数墙缝呢,难不成是托梦签的字?"
李建国的脸唰地褪成宣纸色,威士忌杯坠地的脆响,比吉庆街夜市摔碎的啤酒瓶更刺耳。陈军盯着他手腕上的淤青 —— 那形状,跟中心医院病床上那个经销商额头的伤口如出一辙,像是用同个模子刻出来的。"是你让人开了他的瓢吧?" 警察的手铐 "咔嗒" 锁上时,陈军的皮鞋正碾着对方颤抖的影子,"现在人证物证都齐了,你还有么嘶屁好放?"
下山的风裹着木兰山的雾气,陈军接电话时,曲俊的声音疲惫得像泡透了水的棉絮:"李建国那瑞士账户,户主是林震南的崽林浩。" 顿了顿,江风里飘来更沉的叹息,"香港廉政公署刚传信,林浩在牢里自缢了,死前咬出二十多个香港大佬,里头就有当年跟你外公抢码头的林家老爷子。"
曲丽办公室的百叶窗把阳光切成细条,在文件上织成张金色的网。最上面那张合影里,李建国和王海站在维多利亚港前,背后的游艇船身 "宏业集团" 四个字被刮掉一半,像道没长好的伤疤。"他们早就勾肩搭背了," 她指尖点着照片里的浪花,"这船是林家的,去年被四海集团拍走时,船底还粘着阳逻港的淤泥呢。"
陈军撞开会议室门时,报纸头版的标题能晃瞎人眼:"四海集团宣告破产,董事长王海涉嫌多项罪名被捕"。他把报纸拍在桌上,发现曲俊正盯着份新合同 —— 甲方签名处的笔迹,跟林浩留在监狱登记表上的一模一样。
"这是个套。" 曲俊合上合同的动作,像在拍死只吸血的蚊子,"林家想借壳还魂,用香港公司接着拿捏武汉市场。" 他望向窗外,江面上的货轮正鸣笛驶过,"但他们忘了,武汉的码头,从来就不是外来户能说了算的。"
曲丽的手机突然唱起《洪湖水浪打浪》,洛杉矶设计师举着新款童装出现在屏幕里,好莱坞标志在他身后泛着夕阳的金。"曲总监,新品发布会定在下礼拜,要不要请武汉的合作伙伴来耍耍?"
曲俊突然笑出声,震得茶杯盖都跳了跳:"跟设计师说,把发布会搁长江游轮上办。" 他抓起笔,在合同背面圈出三个名字 —— 李建国、王海、林浩,然后划了个大叉,"让他们瞧瞧,新世纪传媒不光守得住武汉的摊,还能把生意做到天边去。"
长江游轮的甲板上,彩旗在江风里扯着嗓子吆喝。曲俊站在船头,看武汉的天际线在暮色里慢慢显形,像幅正在晕开的水墨画。陈军递来香槟,绷带在白西装下若隐若现,活像根藏在绸缎里的钢筋。"李建国的案子已送检察院,四海集团的资产正在拍卖," 他指着阳逻港方向,江雾里隐约能看见吊臂,"我们拍下了他们在码头的仓库,以后进口有机棉,就跟从自家冰箱拿菜似的方便。"
曲丽牵着莉莉走来,小姑娘穿的新款童装比江花还艳,手里熊猫玩偶的黑眼睛,亮过岸边的航标灯。"汤姆说美国合作方想在武汉建研发中心," 她望着江面碎成星子的灯光,"往后咱不光能往外运货,还能输出设计和规矩。"
游轮鸣笛时,江豚突然跃出水面,银亮的脊背划破暮色。曲俊望着岸边渐小的人影,突然想起父亲说的:"天涯再远,心里有家,走到哪都不算漂泊。" 他举杯对着阳逻港一饮而尽,香槟的气泡在舌尖炸开,像极了外公当年在码头看见的烟花 —— 那些在 1983 年除夕绽放在江面上的光,此刻正从记忆深处浮上来,混着江风落进酒杯里。
夜色中的长江活成了条奔腾的龙,驮着新世纪传媒的梦往远天游去。武汉的码头却依旧灯火通明,起重机的铁臂在雾里屈伸,像群守护城池的巨人。它们见过民国时的洋行,见过抗战时的硝烟,见过改革开放后的集装箱,如今正睁大眼睛,等着看更多像曲俊、陈军、曲丽这样的人,把新的故事刻进江滩的石头里。
汽笛声还在江面上打旋,曲俊的手机在西装内袋里震动,像揣了条不安分的鱼。陌生号码的归属地闪着 "香港",接通后传来的声音,糙得像被砂纸磨过的船板:"曲总,林老爷子咽气前,让我把这个交你。"
陈军正扶着栏杆吐酒,听见这话猛地转身,香槟杯摔在甲板上的声音,惊飞了船舷上栖息的夜鹭。"是林家的老管家福伯," 他抹了把嘴,酒液在下巴上画出歪歪扭扭的河,"当年你外公在码头被人推下水,就是他第一个跳下去捞人的。"
曲丽的指尖在手机屏幕上飞,调出的资料里,七十岁的福伯坐在养老院藤椅上,左眉骨那道疤像条卧着的蜈蚣 —— 跟当年码头监控里那个模糊身影的特征,能对上榫卯。"他为啥现在才联系咱?" 她放大照片,老人浑浊的眼睛里,似乎藏着整条长江的秘密。
游轮靠岸时,海关的人已在码头站成排,黑制服的影子被灯光拉得老长,像道没画直的警戒线。为首的中年男人亮证件时,胸前编号在灯影里跳着迪斯科。"收到举报,说你们游轮藏了走私的有机棉。" 他手一挥,十几个身影立刻冲上船,翻箱倒柜的动静,比吉庆街夜市的喧闹还甚。
曲俊突然笑了 —— 这男人梳着油亮的背头,西装熨得比镜子还平,但那双手腕上的老年斑,跟李建国那个拾荒表舅的一模一样。"看来林家的余孽,比热干面里的芝麻酱还多。" 他对陈军使个眼色,后者悄悄摸出鞋底的刀片,割断行李箱绑带的动作,比切藕带还利落。
海关人员悻悻离去时,车后窗里有双眼睛正通过望远镜瞄着甲板。那侧脸在路灯下忽明忽暗,鹰钩鼻的弧度,跟老照片里的林震南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—— 是林家长孙林伟,去年从伦敦大学毕业,学的国际贸易,听说论文写的是《论长江中游港口的走私潜力》。
"林伟想接他老子的班," 曲丽划着对方的社交账号,最新动态定位在武汉天地的西餐厅,发布时间就在半小时前,"他身边那女的,是武汉海关关长的千金,这是想把闸门凿个洞啊。"
陈军突然捂住伤口龇牙咧嘴,冷汗顺着鬓角往下淌,像刚从江里捞出来似的。"我让兄弟们去查了,林伟在武汉天地租了套公寓,里头藏着不少林家的旧部。" 他掏出张皱巴巴的纸条,"有两个是当年走私的船员,现在改头换面,在阳逻港当调度员,跟藏在米缸里的老鼠似的。"
第二天清晨,阳逻港的吊臂在雾里站成沉默的巨人。曲俊带着陈军走进调度室时,两个男人正对着电脑指指点点,屏幕上货轮信息的目的地写着 "香港",cargo 栏填着 "普通货物",但备注里那串数字 —— 曲俊一眼就认出来,是林家走私集团的暗号,翻译过来就是 "见不得光的东西"。
"曲总怎么有空来码头逛?" 其中一个调度员站起来,笑容僵得像块冻豆腐。他左手无名指缺了截,那是当年走私集团的标记,据说只有立下 "大功" 的人才有资格自残明志,跟古代的太监似的。
曲俊没接话,径直走到电脑前调出货轮详细信息。"这艘船的实际载重,比申报的多了五十吨。" 他指着屏幕上的吃水线,"这些多出来的,是么嘶好东西?"
调度员的脸瞬间褪成纸色,支支吾吾说不出话。陈军突然从身后锁住他喉咙,另一个想往门外蹿,却被守在门口的保镖逮个正着。"说不说?" 陈军的声音冷得像江底的冰,手上力道越来越大,"再装哑巴,就把你们捆成粽子扔江里喂鱼。"
就在这时,码头广播突然尖叫起来,播放着紧急通知:"所有人员立刻撤离,台风即将登陆!" 调度员趁机挣脱陈军,跟头把式地往仓库跑。曲俊和陈军追过去时,发现他们钻进了个废弃仓库,铁门 "哐当" 关上的瞬间,曲俊仿佛听见了父亲的叹息 ——"武汉的码头是个大染缸,进去了就很难再干净地出来。"
仓库里堆着的木箱散发着刺鼻的化学品味,曲俊撬开一个,里面的白色粉末用保鲜膜层层裹着,上面居然印着新世纪传媒的 logo,跟贴错了标签的毒药似的。"他们想栽赃嫁祸," 曲俊的眼神冷得能结冰,"让我们这辈子都洗不清。"
陈军踹开后门时,调度员正往快艇上爬。追逐战在江面上展开,浪花溅起的高度,比码头吊臂还夸张。曲俊站在仓库门口,看快艇拖着白浪往远处逃,突然觉得这场景很熟悉 —— 二十年前,父亲也是这样站在码头上,看着林家的走私船消失在雾里。
半小时后,陈军押着调度员回来,快艇的引擎还在突突作响,像头刚被驯服的野兽。审讯室里,那人终于松了口:"是林伟让我们干的,他说只要搞垮新世纪传媒,就让我们当阳逻港的总经理,吃香的喝辣的。" 他还供出林伟藏在东湖边的别墅,周围保镖比码头的集装箱还密。
曲俊带人赶到时,别墅大门紧闭,保镖手里的枪在阳光下闪着冷光,跟趴在门后的狼似的。曲俊让陈军带部分人从后门绕,自己在前门喊话,声音撞在院墙上弹回来,惊起一片飞鸟。"林伟,出来吧,躲着像么嘶样子?"
别墅门突然开了,林伟举着枪站在台阶上,黑洞洞的枪口指着曲俊的头。"你以为赢了?" 他笑得比哭还难看,"我手里有林家所有秘密,包括你外公的死因,敢动我就全抖出去,让你们曲家永世不得翻身!"
曲俊往前走了半步,皮鞋碾过阶前的青苔。"真相总有见光的那天," 他的声音比东湖的水还稳,"而你,只会成为林家最后一个罪人,钉在码头的耻辱柱上。"
陈军带着人从后门冲进来时,保镖们的枪声惊飞了满树白鹭。林伟转身想往屋里跑,被曲俊一把抓住后领,手枪掉在地上的脆响,比除夕的鞭炮还清亮。"你跑不掉的。" 曲俊将他按在地上时,看见他脖颈上挂着的玉佩 —— 跟林震南老照片里戴的那块一模一样,只是裂纹更密了。
别墅地窖里搜出的账本,厚度能赶上《武汉通史》。泛黄的纸页上记录着林家从民国到现在的走私史,照片里的码头工人汗流浃背,录音带里的交易对话夹杂着江涛声。曲丽联系香港廉政公署时,指尖在键盘上飞舞的速度,比码头上的起重机还快。
当林伟被押上警车时,东湖的水波正拍打着岸边的柳树。曲俊望着远去的警灯,突然想起福伯在电话里说的:"林家欠曲家的,该还了。" 老人送来的那个旧木箱里,装着外公当年的日记,最后一页写着 1953 年的夏夜 ——"震南说要跟我合伙做正当生意,但愿不是骗我的。"
商业战争落幕那天,武汉下了场暴雨。曲俊、陈军、曲丽站在汉街写字楼楼顶,看雨水把城市洗得发亮。长江在脚下奔腾东去,像条写满故事的绸缎,阳逻港的吊臂在雨幕里缓缓移动,正在装卸来自全球的集装箱。
"我们总算成了。" 曲丽的声音混着雨声,眼角的泪光比江面上的波光还亮。陈军咧嘴笑时,伤口的绷带又渗出些红,在白衬衫上洇成朵不规则的花。"付出这么多,总该有回报。"
曲俊望着远方正在建设的长江新区,那里的吊塔像群年轻的巨人。"这只是开始," 他的声音被风吹得很远,"以后要让新世纪传媒的招牌,挂在纽约第五大道,挂在巴黎香榭丽舍,让全世界都知道,武汉的码头能驶出最好的船。"
夕阳破云而出时,给三人镀上了层金边。江面上的货轮鸣笛致敬,惊起的水鸟排成人字形,往更开阔的江面飞去。新世纪传媒的广告牌在雨后闪着光,"诚信经营,品质为先" 八个字,比黄鹤楼的铜顶还亮。
有人说,武汉的码头从来就不缺故事。从民国时的洋行博弈,到改革开放后的商海沉浮,每个浪头里都藏着传奇。而曲俊知道,最好的故事永远在下一页 —— 就像长江永远奔涌向前,码头的吊臂永远向着天空伸展,那些在江风中猎猎作响的旗帜,总会吸引更多追梦人,把足迹刻进这座城市的年轮里。
当第一缕晨光掠过长江二桥的钢索,新世纪传媒的车间已经响起机器声。新到的有机棉散发着阳光的味道,缝纫工人们手指翻飞,把武汉的温度缝进每件童装里。仓库外,集装箱正被吊上货轮,它们将带着这些衣服,驶向全球的港口,就像带着这座城市的心跳,去往世界每个角落。
而在阳逻港的老码头上,福伯种下的那棵樟树已经枝繁叶茂。树下的石碑上刻着行字:"江水汤汤,商道煌煌;守正出奇,方得始终。" 偶尔有孩童跑到树下玩耍,拾起落在地上的樟树籽,那形状,像极了码头工人汗滴的模样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