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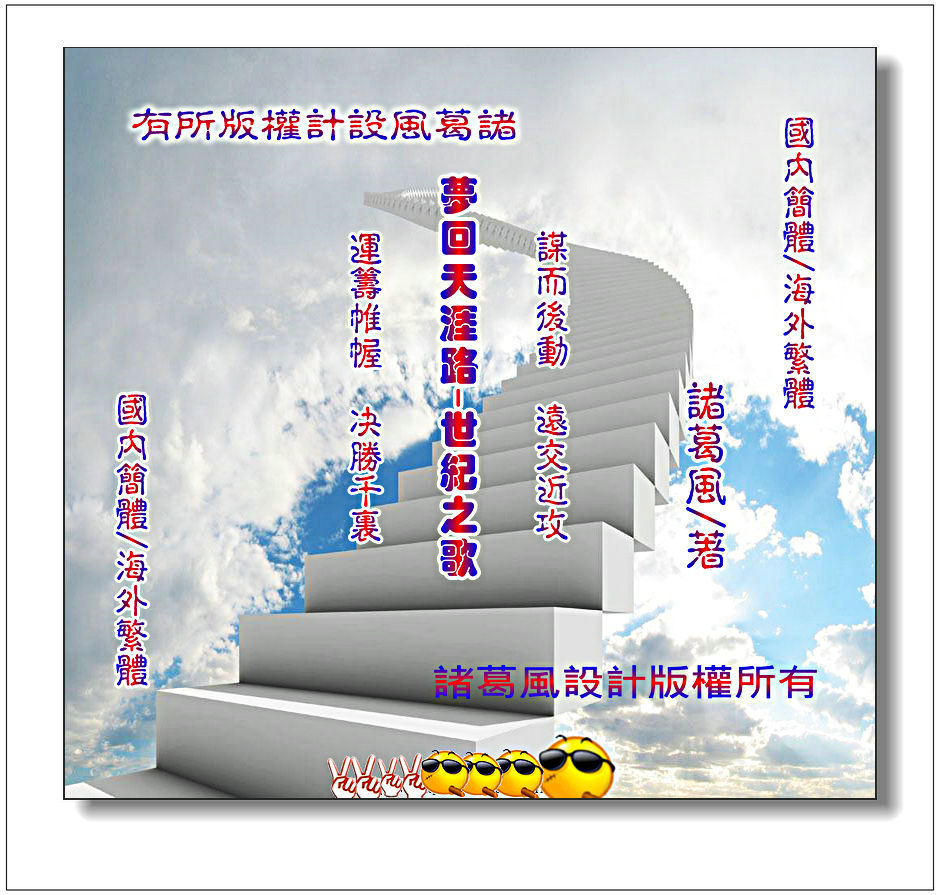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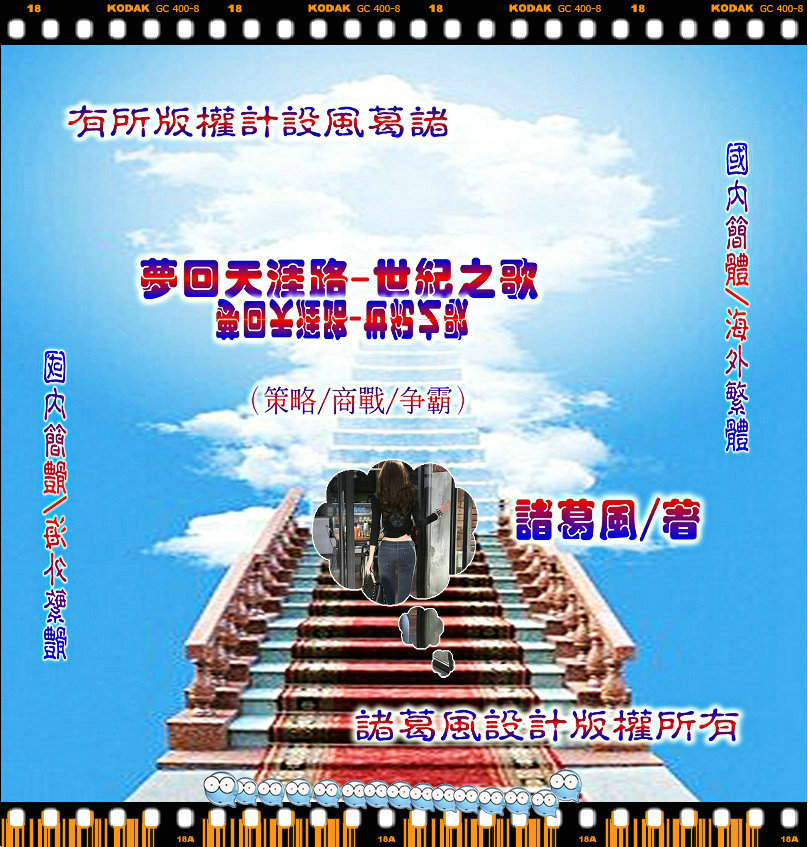
第一百二六章.釜底抽薪
陈军的军靴碾过地上的碎玻璃,咔嚓声跟咬脆骨似的 —— 那是昨晚被人用石块砸的。“楚记纱厂的少东家楚峰,昨晚在江滩的酒吧被人开了瓢,” 他戳着监控截图里的黑影,“下手的人用的开山刀,刀背上的龙纹和当年林家的一模一样,生怕别人不知道是道上的。”
曲丽踩着满地的契约碎片走来,高跟鞋跟嵌进张民国时期的股票,纸渣簌簌往下掉。“楚记纱厂的地契在老子手里,” 她突然拍了下额头,想起外公日记里的话,“1948 年外公帮楚家还清了欠汇丰银行的贷款,楚老爷子把纱厂三成股份抵给了裕昌行,后来时局一乱,这事就跟沉江的货轮似的没人提了。”
酒吧的霓虹灯在江面上碎成金箔,晃得人眼晕。楚峰捂着流血的胳膊,趴在吧台上,威士忌洒了一地,空气中飘着股消毒水混酒精的怪味。“是‘粤帮’的人干的,” 他咳出的血沫染红了领结,跟开了朵烂桃花,“他们想买下楚记的设备,转产假冒的有机棉,老子不答应,就被他们……” 话音未落,包厢的门被踹开,五个穿花衬衫的人举着砍刀冲进来,为首的刀疤脸露出腰间的蟒蛇纹身 —— 是广州 “粤帮” 的堂主雷彪,去年在深圳的纺织品博览会上,因抢订单捅伤过三个同行,出了名的手黑。
陈军突然掀翻吧台,酒瓶滚落的脆响中,他甩出铁链缠住雷彪的手腕。铁链的锈迹蹭在对方的劳力士表上,表盘里映出江面上的游艇 —— 楚记纱厂的设备正被往船上吊装,船身上的 “粤海集团” 字样在夜色中格外刺眼,跟块狗皮膏药。
混战中,曲俊认出雷彪口袋里的地契副本,上面的签名歪歪扭扭一看就是伪造的,却盖着个鲜红的公章 —— 是市公证处的,编号与三天前被盗的那枚一致,真是胆大包天。“你们买通了公证处的人,” 他一脚踹在雷彪的膝盖上,对方的惨叫里混着骨头碎裂的闷响,跟杀猪似的,“楚记纱厂的土地属于历史保护建筑,谁也别想动,当武汉的文保部门是摆设?”
雷彪的手机从裤袋滑落,屏幕亮起的瞬间,曲丽看清了通话记录 —— 最近的一个号码属于市规划局局长。“难怪你们敢这么明目张胆,” 她突然想起今早收到的匿名邮件,附件里的照片显示,局长正和粤海集团的董事长在澳门的赌场握手,笑得跟朵菊花似的,“粤海集团想借旧城改造的名义,把楚记纱厂的地改成商业综合体,容积率超标三倍,这是想把黄鹤楼都给挤塌?”
市公证处的档案室突然传来警报,跟狼嚎似的。陈军带着人冲进去时,三个蒙面人正用碎纸机销毁证据,地上的纸屑里混着张楚记纱厂的股权证明,上面的签名是楚峰的父亲,日期却是他去世后的第三天,这造假水平也太业余了。“粤帮的人早就策划好了,” 陈军揪住个蒙面人的头发,扯下的头套露出张熟悉的脸 —— 是公证处的副科长,上个月还来新世纪传媒参加过招商会,端着酒杯说要 “共建美好武汉”,脸皮比江滩的铁板还厚。
楚峰躺在同济医院的 VIP 病房里,输液管里的药水在阳光下泛着微光,跟掺了金粉似的。“我爸临终前说,楚记纱厂的仓库里藏着样东西,” 他突然抓住曲俊的手,跟抓救命稻草似的,“是台 1937 年的德国织布机,能织出比有机棉更细密的面料,当年希特勒的军服就是用这种布做的,硬得能当铠甲。”
仓库的铁门被焊死了,陈军用氧焊切割时,火星溅在墙角的木箱上,燎起层黑灰。箱子里的织布机蒙着厚厚的灰尘,铜制的齿轮上刻着纳粹的鹰徽,看着有点瘆人。曲丽突然发现机座下的暗格,里面的羊皮卷上,用德文写着 “莱茵集团” 的字样 —— 和汉斯博士祖父留下的徽章上的一模一样,真是无巧不成书。
粤海集团的董事长周粤生突然出现在病房门口,手里的雪茄烟雾缭绕,跟个移动烟囱。“曲总,开个价吧,” 他弹了弹烟灰,灰渣落在锃亮的皮鞋上,“楚记纱厂的设备加土地,我出三个亿,够你们在欧洲开十家分店了,别不知好歹。” 他的金表链上挂着枚玉佩,和楚峰脖子上的那枚正好组成一对 —— 是楚家的传家宝,据说能打开纱厂的地下金库,搞得跟武侠小说似的。
曲俊突然将羊皮卷拍在桌上,周粤生的瞳孔骤然收缩,跟见了鬼似的。“1938 年莱茵集团给楚记纱厂投过资,” 他指着卷末的签名,“你的祖父周大海当时是翻译,后来卷走了这笔钱,在香港开了家纺织厂,也就是现在的粤海集团,说起来你们还是靠骗来的钱发家的?”
周粤生的雪茄掉在地上,火星在地毯上烧出个黑洞,跟他的心眼一样黑。“看来你们查得很清楚,” 他突然从怀里掏出手枪,枪口指着楚峰的头,“但你们别忘了,武汉的码头谁说了算,不是看历史,是看实力!”
病房的窗户突然被撞碎,玻璃碴子溅了一地。陈军带着人从消防通道闯入,橡胶棍砸在保镖头上的闷响中,曲丽认出其中一个保镖的纹身 —— 是蛇帮的,坤沙在狱中的徒弟,真是臭味相投。“粤海集团和蛇帮勾结,” 她对着对讲机大喊,“把他们的交易记录发给出入境管理局,我就不信查不到他们走私的证据,非得把这群蛀虫挖出来不可!”
地下金库的门被打开的瞬间,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,冷气差点把肺冻住。金条堆成的小山旁,放着台老式电台,摩斯密码的纸带还在缓缓转动,跟有鬼魂在操作似的。曲俊认出上面的代码 —— 是二战时期盟军的加密方式,翻译过来的内容让他浑身冰凉:“楚记纱厂生产的特种面料,已通过粤帮运往东南亚,用于日军军服……”
楚峰突然跪倒在地,额头撞在金条上发出闷响,跟磕破了头的西瓜。“我对不起祖宗,” 他的哭声在金库回荡,跟狼嗥似的,“我爸就是因为发现了这个秘密,才被粤帮的人害死的,这笔血债必须偿!”
周粤生被按在金条上时,突然狂笑起来,笑得眼泪都出来了:“你们以为赢了吗?楚记纱厂的地已经被抵押给了香港的银行,明天就会被拍卖,到时候你们什么都得不到,竹篮打水一场空!”
曲俊掏出手机,屏幕上是和香港汇丰银行行长的视频通话记录,画面还热乎着。“我们已经替楚家还清了贷款,” 他举起新的地契,纸页在灯光下泛着白光,“从今天起,楚记纱厂由新世纪传媒接管,我们会恢复生产,让武汉的老字号重新焕发生机,总比落在你们这群蛀虫手里强。”
织布机重新运转的那天,武汉下起了小雨,跟老天爷在洒泪。曲俊站在车间里,看着楚峰调试设备,德国齿轮转动的声音和八十多年前一样清脆,跟时光在唱歌。陈军带着人在厂区巡逻,腰间的枪套里别着枚新的徽章 —— 是楚记纱厂的厂徽,铜制的齿轮上刻着 “1927-2009”,见证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。
曲丽的手机突然响起,是巴黎总部发来的视频。皮埃尔站在埃菲尔铁塔下,手里举着件楚记纱厂生产的面料样品,激动得脸都红了:“这种面料在欧洲引起了轰动,香奈儿、迪奥都想和我们合作,曲总监,我们要发财了,发大财了!”
江面上的货轮鸣响汽笛,笛声在江面上荡出圈圈涟漪,载着楚记纱厂的面料驶向世界各地。曲俊站在码头,看着夕阳将江面染成金色,跟铺了层金砖。突然想起外公说过的话:“武汉的码头,能装下整个世界,也能承载所有的历史。” 他掏出那对纯金船锚吊坠,在余晖中合二为一,仿佛看到外公和楚老爷子站在当年的码头,对着远方的货轮微笑,跟两个骄傲的老船长。
夜色中的楚记纱厂灯火通明,织布机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,像是在诉说着一个跨越世纪的传奇。而新世纪传媒的故事,还在继续上演,在武汉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,书写着属于他们的天涯路,路的尽头,是更广阔的世界。
楚记纱厂的织布机刚运转满一个月,汉阳铁厂的烟囱就喷出了异常的黑烟,跟条黑龙似的。曲俊站在汉街写字楼的落地窗前,望远镜里的黑烟在晨光中扭曲成狰狞的形状,看着就晦气。“刚收到环保局的通知,” 他放下望远镜,指尖在桌面上划出黑烟的轨迹,“汉阳铁厂的废水超标排放,污染了我们在沌口的有机棉种植基地,土壤检测报告显示重金属含量超标三倍,这是想把我们的地变成毒地?”
陈军的军靴在地板上踏出沉重的声响,跟打夯似的。他刚从沌口赶回来,裤脚还沾着黑色的污泥,跟在泥里打了滚。“种植基地的工人说,昨晚看到汉阳铁厂的人偷偷往灌溉渠里排放废水,” 他掏出手机里的照片,照片上的阀门还在滴着黑色的液体,跟流脓似的,“为首的人是汉阳铁厂的副厂长赵刚,他胳膊上的狼头纹身和当年粤帮的雷彪一模一样,又是这群杂碎。”
曲丽踩着高跟鞋走进来,鞋跟敲地的声音跟敲算盘似的。手里的文件夹上印着 “汉阳铁厂” 的字样,纸页都被她捏皱了。“汉阳铁厂的董事长是赵天雄,” 她调出赵天雄的资料,照片上的男人穿着中山装,胸前的口袋里插着支钢笔,装得跟文化人似的,“他是赵刚的堂哥,据说和香港的‘洪兴社’有来往,去年在香港的房地产拍卖会上,用暴力手段抢走了三块地皮,就是个地痞流氓。”
织布机的轰鸣声在楚记纱厂的车间里回荡,震得人耳朵嗡嗡响。楚峰正在调试那台 1937 年的德国织布机,突然发现织出的面料上出现了不规则的纹路,跟长了牛皮癣。“是染料有问题,” 他拿起染料桶,桶底的沉淀物泛着黑色的光,“这种染料含有大量的甲醛,是从汉阳铁厂的废料里提炼出来的,这群丧良心的,想害死多少人?”
陈军带着人赶到汉阳铁厂时,赵刚正指挥着工人往卡车里装废料,忙得跟投胎似的。“曲总真是消息灵通,” 赵刚的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容,跟庙里的恶鬼,“这些废料要是卖给小作坊,能赚不少钱呢,你管得着吗?” 他突然从腰间抽出一把匕首,匕首上的寒光在阳光下闪得刺眼,“你们要是识相,就别管闲事,否则别怪我不客气,白刀子进红刀子出!”
陈军没有退缩,他从身后抽出一根铁棍,铁棍在阳光下泛着冷光,跟条铁蛇。“赵厂长,你这是在犯法,” 他的声音冰冷,跟寒冬的江风,“污染环境是要负刑事责任的,你要是现在收手,或许还能从轻发落,别一条道走到黑。”
赵刚冷笑一声,挥舞着匕首冲了上来,跟疯狗似的。陈军侧身躲过,铁棍横扫过去,正中赵刚的膝盖。赵刚惨叫一声,跪倒在地,匕首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,跟丧钟似的。“你敢打我,” 他捂着流血的膝盖,眼中充满了怨毒,“我堂哥不会放过你的,他会把你碎尸万段!”
就在这时,汉阳铁厂的大门突然打开,赵天雄带着一群打手冲了出来,跟一群饿狼。打手们手里拿着钢管和砍刀,气势汹汹地朝陈军他们扑来。“敢动我弟弟,你们找死!” 赵天雄的声音像打雷一样,震得人耳朵发疼,唾沫星子横飞。
陈军立刻让兄弟们做好战斗准备,他自己则拿着铁棍迎了上去,跟个拼命三郎。钢管敲击在铁棍上的闷响、砍刀划破空气的锐响、惨叫声、怒骂声交织在一起,在汉阳铁厂的厂区里回荡,跟场交响乐,只不过奏的是地狱的调子。
曲俊和曲丽赶到时,战斗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,跟一锅乱炖。曲俊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,然后带着曲丽冲进人群,试图阻止这场混战。“赵董事长,住手吧,” 曲俊对着赵天雄大喊,嗓子都快喊破了,“再打下去,对谁都没有好处,非要闹到人命关天吗?”
赵天雄根本不理会曲俊的话,他挥舞着拳头,打得一个工人鼻血直流,跟开了个血喷泉。“我赵天雄在武汉混了这么多年,还没人敢管我的闲事,” 他瞪着曲俊,眼睛里布满血丝,“你要是识相,就赶紧带着你的人滚,否则我连你一起收拾,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!”
警察的到来终于制止了这场混战,跟天降神兵。赵天雄和他的打手们被警察带走,赵刚也因为涉嫌污染环境被依法逮捕,真是大快人心。曲俊看着他们被押上警车,长长地舒了一口气,感觉浑身的骨头都松了。“这场仗,我们赢了,” 他对陈军和曲丽说,“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,赵天雄在武汉的势力很大,他肯定会报复我们的,跟条毒蛇似的。”
果然,没过多久,新世纪传媒在汉口的门店就被人砸了,跟被台风过境似的。监控录像显示,动手的人是一群蒙面人,他们手里拿着钢管和砍刀,将门店里的货架和商品砸得稀巴烂,跟疯了似的。曲俊认出其中一个蒙面人的体型,和赵天雄的一个贴身保镖一模一样,不用猜都知道是谁干的。
“赵天雄这是在向我们示威,” 陈军的眼中闪过一丝怒火,拳头捏得咯咯响,“我现在就带人去砸了他的汉阳铁厂,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,以牙还牙!”
“不行,” 曲俊拦住了陈军,眼神坚定,“我们不能中了他的计。他就是想激怒我们,让我们做出不理智的行为,然后抓住我们的把柄,好反咬一口。” 他沉思了片刻,眉头皱成个疙瘩,“我们要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,让赵天雄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,让他知道武汉是法治社会,不是他的天下。”
曲丽立刻联系了律师,准备起诉赵天雄故意破坏财物。同时,她还让市场部的人收集赵天雄和 “洪兴社” 来往的证据,忙得脚不沾地。“我就不信找不到他的破绽,” 曲丽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,跟藏了星星,“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证据,就能让他身败名裂,把牢底坐穿!”
就在这时,香港的 “洪兴社” 突然派人来武汉,跟闻到血腥味的鲨鱼。为首的人是 “洪兴社” 的堂主陈浩南,他穿着黑色的西装,戴着墨镜,看起来威风凛凛,跟电影里走出来的似的。“赵董事长让我来跟你们谈谈,” 陈浩南摘下墨镜,眼中露出一丝不屑,跟看蝼蚁,“他说只要你们撤销对他的起诉,并且把楚记纱厂让给他,他就不再找你们的麻烦,算是给你们条活路。”
破阵子・楚街砺剑
铁马踏碎江月,金戈挑落星灯。
百年纱厂藏剑影,十里洋场起腥风。
楚河浪未平。
敢向龙潭取契,笑将虎穴为营。
织机犹记当年誓,船锚终合此生盟。
潮头看我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