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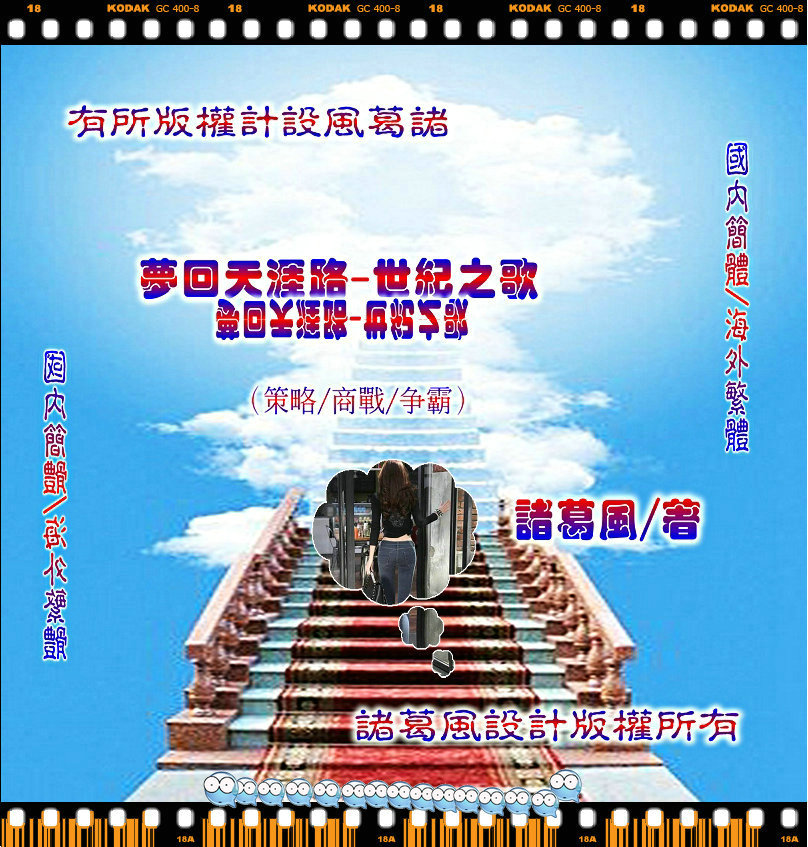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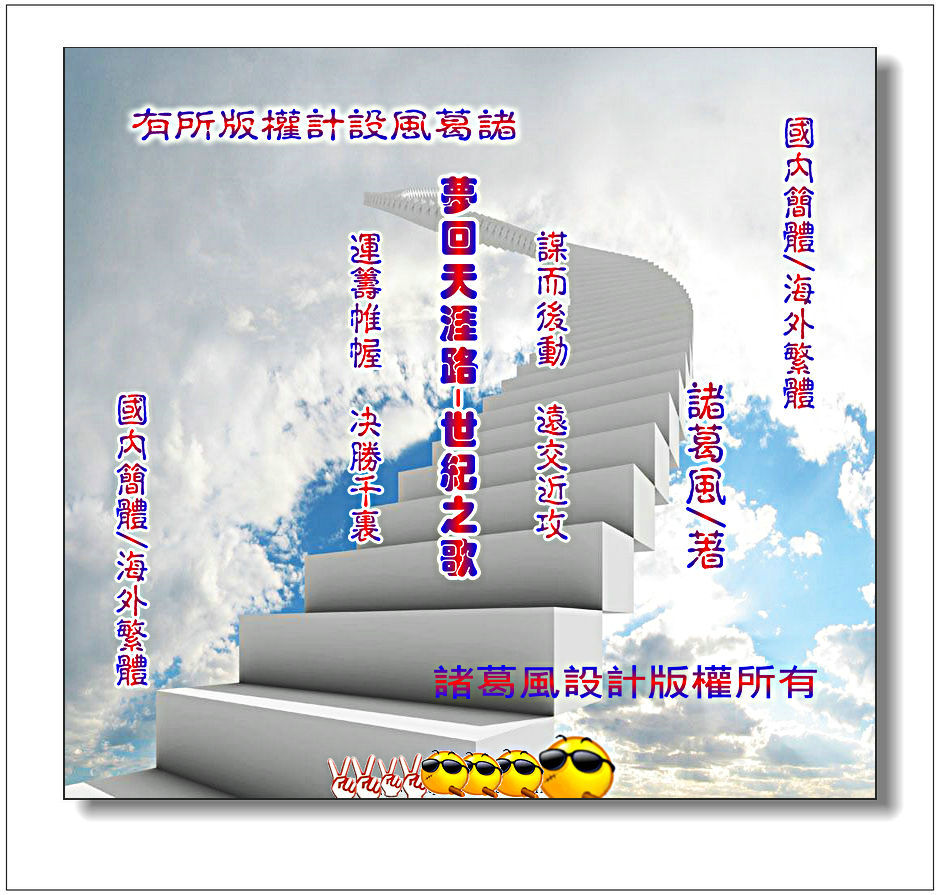
第一百二七章.取长补短
曲俊眯着眼睨着陈浩南,嘴角撇出半截冷笑,像片淬了冰的刀片:“赵天雄当老子是吓大的?派个黄毛小子就想拿捏新世纪传媒?” 他直起身,皮鞋在地板上碾出细碎声响,“回去跟那老东西讲,楚记纱厂的地,他要敢动,先从我尸体上碾过去 —— 哦对了,记得提醒他,老子这骨头硬得很,别硌坏了他的破车。”
陈浩南脸盘子瞬间垮得像块浸了水的抹布,拳头攥得咯吱响。说时迟那时快,他那砂锅大的拳头带着风就抡过来了。曲俊早瞅着他那点花花肠子,腰一拧跟泥鳅似的滑开,回手一拳捣在对方肚皮上。陈浩南疼得像只被踩了尾巴的猫,弓着身子直哼哼。他那帮手下跟炸了窝的马蜂似的围上来,陈军和曲丽也不含糊,抄起旁边的铁凳子就摆出架势。两边人鼻子对鼻子眼对眼,唾沫星子都快溅到对方脸上,眼看就要上演全武行。
“都给老子站住!” 穿制服的跟神兵天降似的撞开大门。陈浩南那帮人跟见了猫的耗子,撒腿就往楼梯口窜。警察同志也不含糊,甩开膀子就追,最后逮着几个跑肚拉稀掉队的倒霉蛋。曲俊望着陈浩南屁滚尿流的背影,眼里那点光比车间里的灯泡还亮:“赵天雄,这笔账,老子跟你慢慢算。”
接下来几天,武汉商界跟起了霉雨,空气里都飘着股火药味。赵天雄的汉阳铁厂跟中了邪似的,一会儿机器 “嗝屁”,一会儿工人 “撂挑子”,生产线停得比茶馆里说书先生的快板还有节奏。新世纪传媒倒跟捡了漏的麻雀,趁机把摊子铺得老大。他们那有机棉织的料子,摸着手感跟绸缎似的,街坊们抢得跟不要钱似的,连带着汉口老街坊都念叨:“还是楚记纱厂的布,经穿!”
曲俊心里跟明镜似的,这平静跟暴风雨前的蚊子似的,嗡嗡几声就得炸锅。赵天雄和他那 “洪兴社”,指不定憋着什么坏水。但他怕个球?反正光脚的不怕穿鞋的,只要自个儿腰杆子硬,管他来什么妖魔鬼怪。楚记纱厂的织布机转得欢实,咔嗒咔嗒跟唱小调似的,织出的料子一车车往全国各地送。曲俊站在车间里,看工人们手脚麻利地穿梭,脸上那笑跟喝了孝感米酒似的,甜到心坎里。这厂子可是武汉工业的活化石,从民国撑到现在,他凭什么让它栽在自个儿手里?
正琢磨着,车间大门 “哐当” 被撞开,一个小工跑得跟被狗撵似的:“曲总,糟了!赵天雄带了一群人,跟拆房子似的往厂里冲!”
曲俊脸一沉,对陈军扬下巴:“抄家伙!”
陈军二话不说,招呼工人们拿起扳手、钢管,那架势跟要去打群架的码头工人似的。曲丽倒机灵,猫到角落就摸出手机:“喂,警察同志吗?楚记纱厂有人闹事,跟黑社会似的……”
赵天雄带着一群打手跟饿狼似的扑进车间,手里钢管砍刀闪着寒光,见着机器就抡。“曲俊,你个龟儿子没想到吧?” 赵天雄笑得跟偷了鸡的黄鼠狼,“今天就让你尝尝,什么叫一无所有!”
曲俊懒得跟他废话,就那么冷冷地瞅着。等那帮打手冲到跟前,他嗓子跟炸雷似的吼:“搞!”
陈军带着工人们跟潮水似的涌上去,扳手对钢管,木棍对砍刀,车间里顿时跟开了锅的粥,叮叮当当的声响比过年放鞭炮还热闹。惨叫声、骂娘声混在一块儿,活脱脱一个战场。
曲俊亲自对上赵天雄。他虽说没正经练过,但跟车间里钻了十几年,身手灵活得跟猴子似的,几次都从赵天雄刀下溜过去。赵天雄气得跟疯狗似的,砍得越来越狠。就在这节骨眼,警笛声跟救火车似的由远及近,警察同志跟下饺子似的涌进来,三下五除二就把赵天雄那帮人铐成了串。
看着赵天雄被押上警车,曲俊才敢松口气,走到陈军旁边拍他肩膀:“赢了。”
陈军脸上汗珠子混着血道子,笑起来跟哭似的:“是咧,赢了。”
曲丽从角落里挪出来,手还抖得跟筛糠似的:“吓死个人,幸好警察来得快,再晚点,机器都得被拆成废铁。”
织布机又转起来了,跟啥都没发生过似的。但曲俊心里门儿清,这架打得跟麻将牌似的,推倒了还能再码起来。武汉商界这潭水,深着呢,底下藏着多少虾兵蟹将谁也说不清。但他怕个锤子?只要他跟陈军、曲丽拧成一股绳,就算天塌下来,也能扛着走。
夕阳把车间染成金红色,织布机和工人们都镶上了层金边。曲俊站在门口,心里跟打翻了五味瓶。往后的路长着呢,但他脚底下跟粘了 502 似的,稳得很。
赵天雄被拉走的第二天,武汉下起了毛毛雨,跟老天爷哭丧似的。楚记纱厂的机器转是转了,但车间里气氛跟追悼会似的,闷得人喘不过气。曲俊盯着那台 1937 年的德国织布机,料子在光线下泛着柔光,他却觉得这胜利跟借来的似的,迟早得还。
陈军胳膊上缠着新绷带,昨天的架打得他跟散了架的自行车似的。“刚从看守所回来,” 他递过文件,“赵天雄在里面还不安分,放话要叫香港的‘洪兴社’兄弟来武汉报仇。还有,那老小子把汉阳铁厂的钱捣鼓到海外账户了,数额吓人。”
曲丽拿着份香港报纸走进来,头版照片上陈浩南跟木乃伊似的躺在病床上。“看来赵天雄在香港也不咋地,” 她指着另一则新闻,“香港警察正扫黑呢,洪兴社的堂口被端了好几个,跟端饺子似的。”
曲俊手指在文件上敲着,突然停在 “龙啸天” 三个字上。“这是哪个?”
陈军凑过来看,脸立马跟涂了墨似的:“义联帮的帮主,跟洪兴社是死对头。听说早年在武汉混过,门儿清。赵天雄转移的钱,八成经他的手。”
话音刚落,车间大门被推开,一个穿黑风衣的男人走进来,脸上一道疤从额头拉到下巴,眼神跟刀子似的能杀人。“曲总,久仰,” 他声音跟砂纸磨铁似的,“龙啸天,从香港来拜访。”
曲俊心里警铃跟拉响了似的,但脸上不动声色,给陈军使了个眼色。“龙帮主大驾光临,有何贵干?”
龙啸天笑起来露出黄牙,跟老烟鬼似的:“听说曲总跟赵天雄闹得不愉快?” 他瞥了眼织布机,“他放海外的钱,其实是我的。现在他栽了,曲总该把钱还我吧?”
曲俊脸沉得能滴出水:“那是非法所得,警察已经冻了。龙帮主想要,找法院去。”
龙啸天的笑瞬间没了,眼神凶得跟要吃人:“不给面子?” 他突然从风衣里掏出枪,指着曲俊,“在武汉,还没人敢跟我这么说话!”
陈军立马挡在曲俊身前,手里攥着根铁棍:“这里是武汉,不是香港!动枪?你试试!”
龙啸天冷笑一声,扣动扳机。枪声在车间里炸响,子弹擦着曲俊耳朵飞过,打在织布机上,料子顿时多了个洞。
“给我上!” 龙啸天吼道。他带来的人跟饿狼似的扑上来,手里钢管舞得跟风车似的。
陈军和工人们拿起家伙就上,车间里又成了战场。曲俊趁机拉着曲丽躲到织布机后面观察。龙啸天的人手跟受过训练似的,出手狠辣,陈军他们渐渐有些顶不住。
就在这时,警笛声跟催命符似的来了。龙啸天脸一变:“撤!” 带着人从后门溜了,转眼就消失在雨里。
警察赶到时,车间跟被台风扫过似的。曲俊跟警察说明情况,希望能尽快逮着龙啸天。但警察也头疼:“那家伙滑得跟泥鳅似的,在香港都没抓到过。”
接下来几天,武汉商界跟被泼了凉水的面条,直挺挺的。龙啸天虽说跑了,但他的势力跟霉菌似的,到处都是。新世纪传媒的合作商一个个打电话,跟惊弓之鸟似的:“曲总,对不住啊,有人威胁我,不敢合作了。”
曲俊把烟头摁灭:“怂个屁!现在退了,以后他更嚣张。”
陈军点头:“我让兄弟们加强戒备了,武汉各个角落都放了眼线,龙啸天敢冒头,立马知道。”
曲丽也说:“我联系了其他老板,大家都怕龙啸天,愿意联手。毕竟他在,谁的生意都别想做。”
正说着,曲俊手机响了,陌生号码。他犹豫了下接起来。
“曲总,别来无恙?” 龙啸天的声音跟锯子似的,“你找不着我的。识相的把钱交出来,不然,新世纪传媒就得从武汉消失。”
曲俊眼神跟淬了冰似的:“龙啸天,你吓唬谁?那钱是黑钱,你敢要?我告诉你,迟早让你蹲大牢!”
“好,好,” 龙啸天怒了,“走着瞧!” 电话 “啪” 地挂了。
曲俊捏着手机,指节发白。他知道,这孙子说到做到,更大的麻烦要来了。
几天后的夜里,新世纪传媒的写字楼突然火光冲天,跟烧红的烙铁似的。火舌舔着楼层,跟贪吃的野兽。陈军带着兄弟们跟疯了似的冲进火场,抢文件设备。曲俊和曲丽在外面指挥消防员,嗓子都喊哑了。
折腾到后半夜,火总算灭了,但写字楼跟被啃过的骨头似的,只剩个架子。文件设备烧得跟炭似的。
“肯定是龙啸天干的!” 陈军眼睛红得跟兔子,“老子非宰了他不可!”
曲俊攥着拳头:“哭个屁!楼没了再盖,设备没了再买,只要人在,新世纪传媒就在!”
第二天,曲俊开紧急会议,宣布公司暂时搬去楚记纱厂的办公楼。“写字楼肯定要重建,安保也得加强,不能再吃这种亏。”
武汉的老板们跟赶集似的来慰问,送设备的送设备,送钱的送钱,还有的拍胸脯:“曲总,以后咱们绑在一块儿干!”
曲俊心里暖烘烘的,原来自个儿不是孤军奋战。“必须尽快逮着龙啸天,” 他对陈军和曲丽说,“不能让他再祸害武汉。”
陈军的眼线传来消息,龙啸天躲在一个废弃工厂。他立马带兄弟赶过去,跟打伏击似的。
废弃工厂里阴森森的,破机器堆得跟山似的,垃圾臭得能熏死人。陈军他们猫着腰前进,突然从暗处冲出一群人,双方立马打在一块儿。
龙啸天果然在,手里挥着砍刀跟疯了似的。陈军跟他打起来,两人你来我往,跟耍杂技似的。陈军身手是不错,但龙啸天混黑社会多年,阴招多,渐渐占了上风。
就在陈军快扛不住时,曲俊带着警察赶到了。警察跟包饺子似的把龙啸天一伙人围了,全铐了起来。
看着龙啸天被押上警车,陈军抹了把汗:“总算逮着了。”
曲俊点头,笑了:“是啊,告一段落了。”
龙啸天被抓后,武汉商界总算喘了口气,跟雨后放晴似的。新世纪传媒也开始重建,在大伙帮忙下,渐渐走上正轨。
楚记纱厂的机器转得更欢了,织出的料子不仅在国内卖得火,还漂洋过海到了国外。曲俊站在车间里,看工人们忙碌,那自豪感跟喝了茅台似的,晕乎乎的。他知道,自个儿跟陈军、曲丽的劲儿没白费,不仅保住了厂子,还为武汉争了口气。
夕阳把武汉染成金红色,曲俊、陈军和曲丽站在楚记纱厂楼顶,望着底下车水马龙。
“我们成了,” 曲丽眼里闪着泪花儿。
陈军笑着点头:“是成了,但不能得意,以后的坎儿还多着呢。”
曲俊望着远方,眼神亮得很:“路还长着呢。我们得把新世纪传媒和楚记纱厂做成世界牌子,让武汉的名字,响遍全球!”
他们的声音在夜空中飘着,满是底气。武汉的夜色美得很,灯火跟星星似的,看着这座城市变样……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