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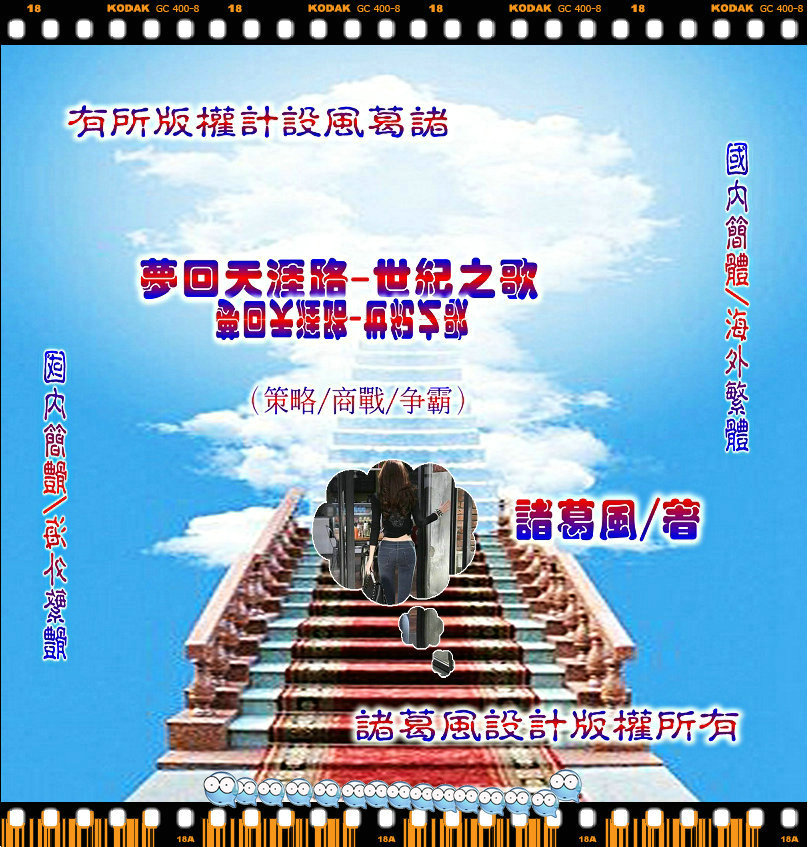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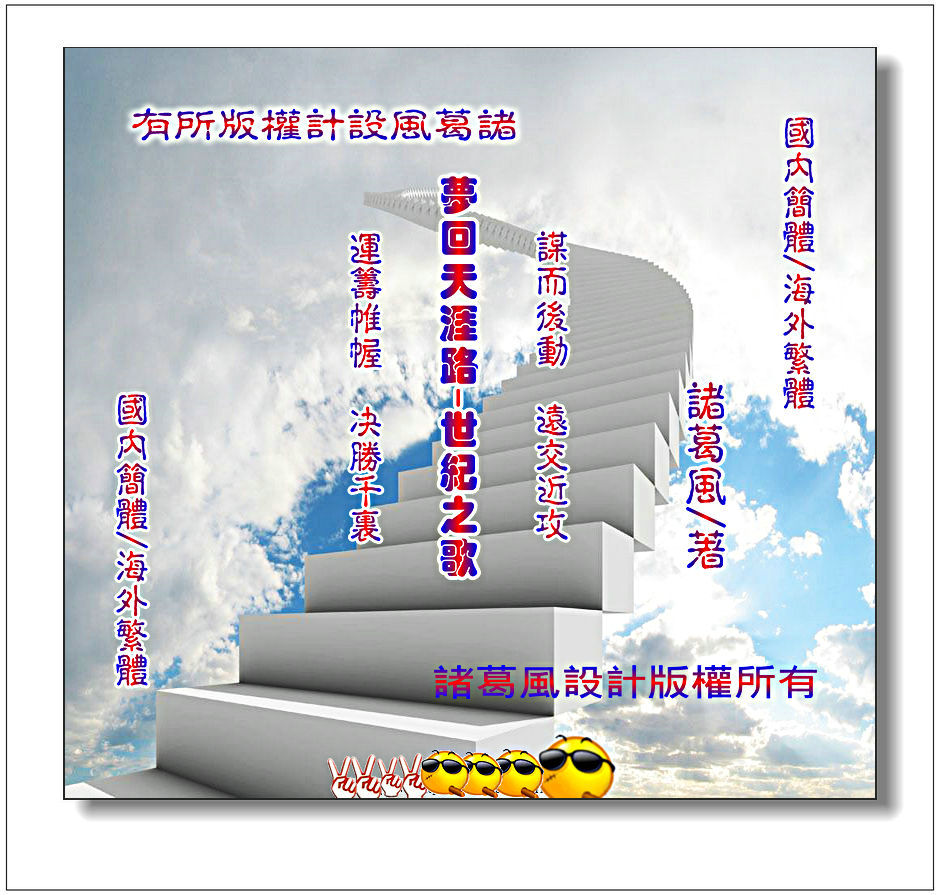
第一百四二章.以他为过
武汉电视台的直播车跟得比街溜子还准时,镜头咔嚓咔嚓把九门堂那帮伙计拍得清清楚楚 —— 一个个被捆得像端午的碱水粽,绳子勒得肉都往外鼓。曲丽举着两件旗袍在镜头前晃,嗓门亮得能压过长江边的货船鸣笛:“您家们看清楚撒!真家伙的盘扣是翡翠雕的,假的?嘿嘿,树脂糊的!里子更不消说,真的是百分百有机棉,假的那是黑心棉,黑得跟夜猫子眼睛样!标签上这防伪码,刮开一扫就晓得,别个哄得了您的钱,哄不了这机器!”
九门堂那九个码头当天就被警方封得严严实实,封条贴得比春联还密。九头鸟跑的时候慌不择路,一头扎进自己挖的暗道里 —— 您猜怎么着?那里面堆的假货能塞满三个集装箱,够他在里面开个假货博览会了。周小辫在号子里哭得涕泗横流,交代说九头鸟原本打算店庆后把楚记纱厂的老织布机炸了,让汉派服装的复原计划彻底打水漂。这心思歹得,比夏天的馊饭还难闻。
楚记纱厂的老织布机倒是给面子,在店庆的鞭炮声里哐当哐当转,织出的图案竟是九头鸟的通缉令。曲俊站在车间里,看着 1937 年的老伙计吐出的纯棉线,被缝进老字号协会合作的第一批汉派服装里,心里跟喝了冰镇酸梅汤似的舒坦。“九门堂那破仓库改造成汉派服装博物馆了,” 曲丽的平板电脑上,设计图闪着光,“下个月开馆,九头鸟的妹妹主动要来当讲解员,说要替她哥赎罪。这转折,比汉正街的巷子还绕。”
陈军的军靴碾过九门堂留下的砍刀,那声音跟啃骨头似的。这些刀后来被熔铸成了织布机的配件,也算废物利用。“刚收到消息,” 他把邀请函拍在曲俊面前,“上海的老字号博览会请我们去,让汉派服装走出武汉,走向全国。这下,咱的旗袍要去见大世面了。”
汉正街的灯笼把新世纪传媒的门店照得红彤彤的,跟过年一样。曲俊站在体验店的阁楼上,看长江上的货轮运走刚出厂的汉派服装,码头工人戴的防割手套还是咱自家产的。九门堂的旧址上,“汉派服装博物馆” 的招牌刚挂起来,老织布机的轰鸣声和汉正街的吆喝声混在一起,像首没头没尾却格外带劲的武汉商业歌。
曲丽的笑声从博物馆里飘出来,她正给孩子们讲楚记纱厂的历史。陈军靠在阁楼栏杆上,手里的铁链缠着枚新奖章 —— 武汉老字号协会发的 “传承奖”,背面刻着 “楚记百年”。曲俊摸了摸体验店墙上的武汉地图,每个区的门店都插着小红旗,突然觉得,最宽的天涯,其实就在脚底下这片土地,跑不掉也丢不了。
老织布机的梭子还在来来回回,织出的面料上,武汉的九座桥和九条街缠成一张网。曲俊心里清楚,只要这机器还转着,新世纪传媒的根就扎在武汉,扎在这些街巷、码头,扎在每个为生活瞎折腾的人心里。
上海老字号博览会的邀请函在曲俊办公桌上躺了三天,汉正街的青石板就被暴雨浇得油光锃亮。陈军从码头带回来的布料样本还在滴水,纤维检测一出来,里头混着玻璃碴 —— 跟九门堂地下作坊的黑心棉成分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“九头鸟的三弟八哥,带着十几个亡命徒躲在黄浦江的货轮上,” 他用铁链撬开样本里的硬物,露出的金属片印着 “沪江纺织”,“这家上海老字号被八哥胁住了,用我们的汉派旗袍设计图造假货,标签上的防伪码高仿得很,扫出来跟真的没两样。这手段,比武汉夏天的蚊子还毒。”
曲丽踩着积水进汉派服装博物馆,刚挂好的 1940 年代旗袍突然从衣架上滑下来,衬里的线头勾住个窃听器。“沪江纺织的总经理赵沪生,是八哥在青帮的同门师兄,” 她调出博览会的展位图,沪江纺织的位置紧挨着咱,中间就隔一米宽的走廊,“他们计划在展会开幕当天,用喷雾弄脏我们的旗袍展品,再让记者拍下来,说楚记纱厂的老工艺不经脏。想得倒美!”
八哥的货轮泊在十六铺码头,他穿件仿楚记纱厂的工装褂子,袖口的盘扣是廉价塑料做的 —— 去年在武汉查扣的九门堂假货里,这种盘扣堆了半间仓库,看得人眼睛疼。“曲总要是识相,” 他的金牙在船舱阴影里闪,“把汉派旗袍的独家代理权让给沪江纺织,上海的利润分你四成,够你把汉街的写字楼再盖高十层。”
曲俊突然抖开件旗袍样品,下摆开衩处露出暗缝,里面的微型摄像头正对着八哥。“你们在旗袍里缝了细铁丝,” 他指着样品的肩部,“比标准重量重 150 克。去年有个模特穿了你们的假货,转身时铁丝扎进皮肤,缝了七针。这亏心钱赚得,晚上睡得着?”
八哥的脸瞬间涨成猪肝色,腰间的匕首 “当啷” 掉地上。他吹声口哨,货轮底舱冲出二十多个拿钢管的打手,钢管上的锈迹跟武汉码头斗殴现场的一个样。“沪江纺织在上海有三十家门店,” 八哥的声音跟砂纸磨钢板似的,“从明天起,只要看见新世纪传媒的广告,我就让人给它泼墨汁!”
陈军的铁链在货轮甲板上甩出弧线,链环缠住为首者的手腕时,对方的袖管滑下露出块纹身 —— 青帮的龙形图案,跟赵沪生办公室的镇纸雕刻一个模子。“你们的假货仓库在苏州河的旧厂房,” 他一脚踹翻旁边的染料桶,靛蓝色的液体溅在打手们的工装上,“去年在那里查出五千件仿冒旗袍,每件的盘扣都用工业胶水粘的,洗一次就掉。这点伎俩,还好意思拿出来现?”
曲俊在货轮导航系统里发现异常航线,最近三次都绕经武汉阳逻港 —— 跟九门堂走私船的轨迹重合。“八哥从武汉运走的不只是布料,” 他指着系统里的 cargo(货物)清单,“还有我们的旗袍纸样,上面有楚记纱厂老艺人手绘的尺寸标注,沪江纺织的假货就是按这个做的,只不过把领口改低了两寸。改这两寸,就把良心改没了?”
上海老字号博览会的布展现场,曲丽正指挥工人给旗袍展品套防尘罩,突然发现罩子的布料不对劲。她扯下罩子,里面的纤维在紫外线灯下显出荧光 —— 沪江纺织的 “杰作”,这种布料会在展出三小时后掉色,去年在杭州的展销会,咱的展品就被这么坑过,想起就来气。
“这些防尘罩是赵沪生派人送来的,” 曲丽的高跟鞋跟碾过罩子,“他们在布料里掺了褪色剂,遇汗渍会加速反应,展会上人一多,汗味就能让旗袍变色。” 她突然按住耳机,里面传来武汉警方的通报:八哥的手下正往展厅的通风管里灌墨水。
陈军带着安保人员冲进展厅控制室,八哥的打手正用扳手拧开通风管的阀门。他甩出铁链缠住对方的手腕,链环弹出的微型喷头瞬间喷出清洁剂 —— 曲丽研发的防污剂,三十秒内就能分解墨水。“你们的墨水是用我们的有机棉废料做的,” 陈军的铁链勒得对方指骨发白,“检测报告显示含有重金属,去年有个记者不小心蹭到,手上起了疹子。害人终害己,晓不晓得?”
博览会开幕当天,赵沪生带着沪江纺织的人堵住咱的展位。他举着件沾墨汁的旗袍,对着围观的记者大喊:“大家快看!楚记纱厂的老工艺就这质量,一碰就脏!” 曲俊突然上前,将瓶清水泼在旗袍上,墨汁瞬间凝成水珠滚落 —— 这是用防污纤维改良过的真旗袍,赵沪生手里的不过是件换了标签的假货。
“真旗袍的面料经过三次防污处理,” 曲俊举起检测报告,“沪江纺织的假货用的是普通棉布,别说墨水,就是茶水洒上都擦不掉。” 他突然扯开假旗袍的衬里,露出的细铁丝在闪光灯下无所遁形,“这种偷工减料的做法,根本对不起老字号三个字。丢不丢人?”
八哥见势不妙,带着人想从展厅后门跑,被陈军的铁链拦住。混乱中,他怀里的账本掉出来,上面详细记录着与九头鸟在狱中的交易 —— 用沪江纺织的股份,换取九门堂在武汉的走私渠道。“你们还计划在展会结束后,放火烧掉我们的展品仓库,” 曲俊捡起账本,“账本上写着呢,用的助燃剂就是武汉九头鸟提供的。算盘打得真精,可惜打错了地方!”
上海警方的防爆犬在仓库里找到十个燃烧瓶,瓶身标签印着 “楚记纱厂专用染料”,里面却是汽油和酒精的混合物。赵沪生被带走时,嘴里还喊:“青帮不会放过你们的!我们在黄浦江的货轮上装了炸弹,和你们的旗袍展品同步引爆!”
曲俊立刻联系上海海事局,在货轮的集装箱里发现定时炸弹,引爆装置的感应器与咱旗袍的盘扣材质一致。“他们在盘扣里装了压力传感器,” 拆弹专家指着引线,“只要有人拿起旗袍,炸弹就会爆炸,这和九门堂在武汉用的手法一模一样。真是狗改不了吃屎!”
博览会闭幕后,沪江纺织因生产假货被吊销老字号认证。八哥的货轮被扣在十六铺码头,从里面搜出的仿冒旗袍足够挂满整个外滩。武汉的九门堂残余势力得知消息,在汉正街的门店前闹事,被陈军带领的联防队员一网打尽,收拾得服服帖帖。
楚记纱厂的老织布机在庆功的鞭炮声里,织出了上海外滩的图案。曲俊站在车间里,看着 1937 年的机器吐出的纯棉线,被缝进发往上海的第一批正版汉派旗袍里。“沪江纺织的老厂房改成了楚记纱厂上海体验店,” 曲丽的平板电脑上,新店的设计图闪着光,“下个月开业,赵沪生的女儿主动来应聘设计师,说要学习真正的老工艺。这倒有点意思。”
陈军的军靴碾过八哥留下的钢管,这些钢管被熔铸成了织布机的配件。“刚收到消息,” 他把证书拍在曲俊面前,“国家工信部授予我们‘中华老字号传承创新奖’,这是湖北唯一获此殊荣的纺织企业。咱这脸,可算给武汉挣回来了!”
汉街的霓虹灯照亮了新世纪传媒的招牌,长江上的货轮正满载着汉派旗袍驶向上海。曲俊站在写字楼的露台上,看着武汉的夜景与黄浦江的灯火在脑海中交织。陈军手里的铁链缠着枚新奖章,背面刻着 “沪鄂同源” 四个字,倒是说得实在。
曲丽的笑声从展厅传来,她正给上海来的客商讲解汉派旗袍的盘扣工艺。老织布机的轰鸣声与黄浦江的汽笛声在空气中共鸣,像首跨越长江的商业交响曲。曲俊知道,只要楚记纱厂的梭子还在转,汉派服装的天涯路,就会从武汉的码头出发,走向更广阔的天地,这是肯定的。
楚记纱厂上海体验店的铜铃刚响过第一百声,武汉汉正街的老字号协会就传来玻璃破碎的脆响。曲俊捏着国家工信部的奖牌,指尖在 “中华老字号传承创新奖” 的烫金字样上摩挲 —— 奖牌的木质底座里嵌着根细针,针头上的锈迹与十路盟的徽记纹路一致。这是武汉新崛起的商会,由八哥的表哥石十路牵头,联合了九门堂、八面风的残余势力,在十个区的菜市场都设了假货摊点,跟蟑螂似的到处爬。
陈军的铁链在老字号协会的青砖地上拖出火星,他刚从汉阳的仓库回来,战术背心上还沾着十路盟的特制辣椒水 —— 这种液体混着咱的有机棉纤维,遇热会释放刺鼻气体,上周在汉正街的斗殴中,三个联防队员被呛得送进医院。“石十路的仓库藏在龟山北路的防空洞,” 他用铁链撬开块松动的地砖,下面的暗道直通长江,“里面堆着五千件仿楚记纱厂的棉衣,填充物是医院的废弃棉花,每斤成本不到五毛钱。黑心钱赚得,晚上不怕鬼敲门?”
曲丽抱着老字号协会的合作计划书走进来,封面的火漆印里混着根黑色线头 —— 是十路盟的标志纤维,去年在九门堂的假货里见过。“他们伪造了我们的授权书,” 她调出市场监管局的通报,上周有七个乡镇超市收到假授权,“石十路想让这些超市低价抛售假货,等我们的正品到货时,市场已经被他们搅乱了。这心思,比蛇还毒。”
石十路的地盘在武昌的白沙洲市场。他坐在辆改装过的三轮车上,车斗里的棉衣堆成小山,每件的领标都绣着 “楚记纱厂”,但针脚歪歪扭扭 —— 是用十路盟的 “快手队” 手工缝制的,这群人中有八个是八面风的老裁缝,最擅长仿冒盘扣工艺。“曲总要是识相,” 他的断指在棉衣上戳出洞,“把老字号协会的冬装订单让出来,十路盟分你两成利,足够你给上海体验店再镶层金边。”
曲俊突然扯开件棉衣,填充物里的玻璃碴簌簌落下,与陈军带回的样本成分完全一致。“你们在棉衣里掺了碎镜片,” 他指着标签上的执行标准,是早就废止的 2008 年版本,“去年有个老太太穿了你们的假货,胳膊被划得全是血痕,医院诊断为三级烫伤 —— 碎镜片反射阳光烤伤的。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,良心被狗吃了?”
石十路的脸瞬间紫涨如猪肝,猛地掀翻三轮车。藏在车座下的砍刀滚落出来,刀柄的防滑纹里嵌着咱的有机棉纤维,去年在阳逻港的走私船里,这种纤维缠了满满三铁链。“十路盟在武汉有一百个流动摊位,” 他的声音像被砂纸磨过的钢管,“从今天起,只要看见新世纪传媒的送货车,我就让人给它扎胎放气!”
陈军的铁链如灵蛇般窜出,链环精准地缠住石十路的手腕。他认出围观的人群里有张熟悉的脸 —— 是八面风的 “风子队” 队长,此刻正举着弹弓瞄准曲丽,弹丸是用咱的盘扣熔铸的。“你们的防空洞通着长江的水下暗渠,” 陈军一脚踹翻旁边的假货摊,“上周有艘摩托艇从那里运走三十箱假货,驾驶员是八哥在黄浦江货轮上的副手。还想瞒多久?”
曲俊在防空洞的深处发现了台老旧的提花机,机身上的楚记纱厂铭牌被凿掉了一半 —— 是 1953 年生产的那批国产设备,三年前在荆州的拆迁工地失踪。梭子里的线是用回收的渔网纺的,上面还沾着河泥,去年在东湖的野鸭身上发现过同样的纤维。
“他们想在下周的冬装订货会上动手,” 曲俊指着提花机旁的染料桶,里面的化学试剂遇水会变成黑色,“十路盟买通了会场的清洁工,准备在我们的样品上泼这种染料,再让记者拍下来,说楚记纱厂的老工艺掉色严重。这些把戏,玩不腻吗?”
冬装订货会的布展现场,曲丽正指挥工人搭建展台,突然发现地毯的纤维里藏着微型摄像头。“这些地毯是石十路的表妹送来的,” 她用镊子夹出摄像头,镜头正对着咱的主打棉衣,“他们在地毯里织了导电纤维,通电后会发热,能让棉衣的填充物结块 —— 去年有个经销商收到过这样的假货,投诉说洗一次就成了疙瘩。真是阴魂不散!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