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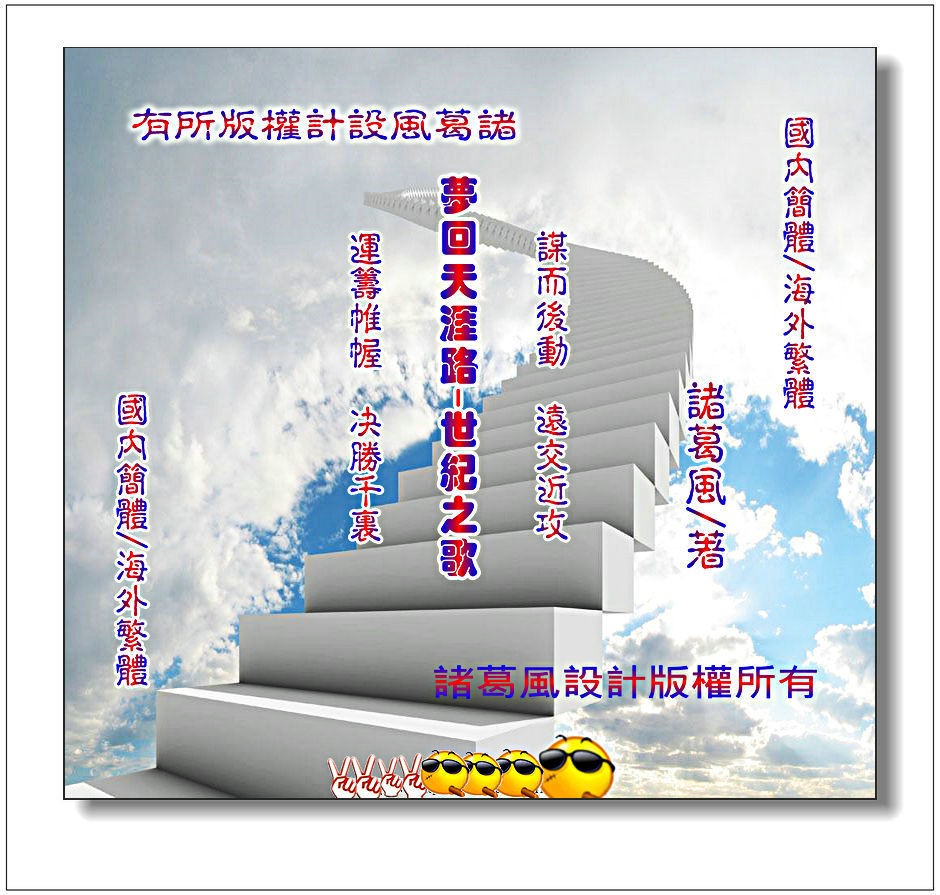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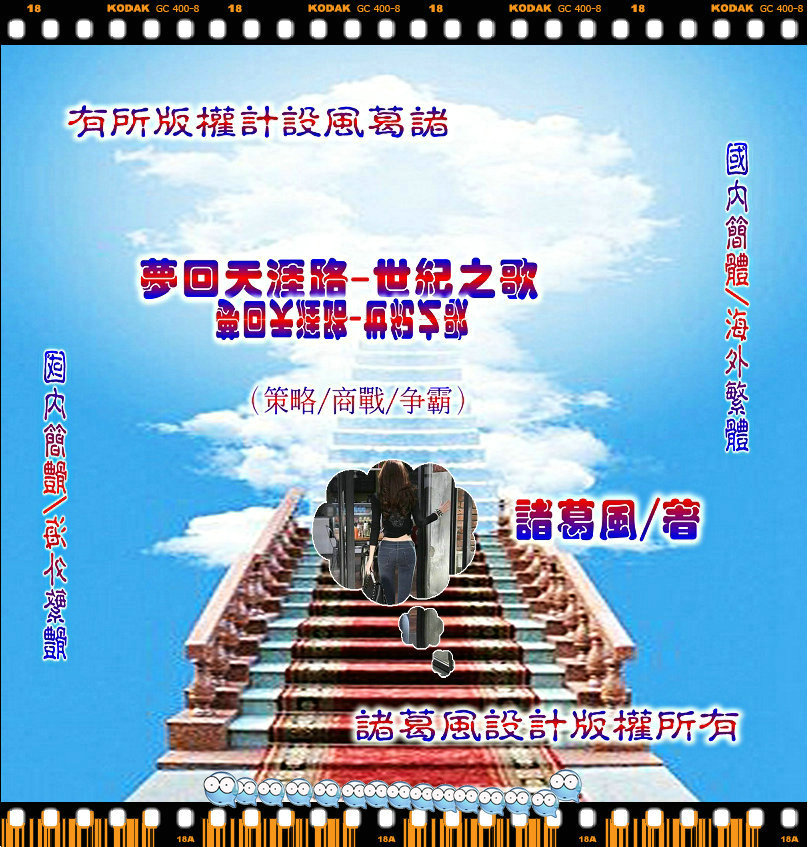
第一百四三章.黄雀在后
钗头凤・织恨
机杼瘦,棉纱旧,百年经纬缠新寇。
盘扣碎,真丝秽,一江浊浪,半城虚伪。
愧!愧!愧!
青石板,灯笼灿,剪刀裁破鱼龙乱。
防污剂,燃瓶计,楚记梭声,未停三纪。
继!继!继!
陈军带着联防队员冲进会场的配电房时,十路盟的电工正往线路里塞金属丝。那架势跟往藕汤里扔老鼠屎似的,忒不地道。他甩出铁链缠住对方的工具包,里面的保险丝全被换成了劣质品,熔断电流比标准低了 40%—— 这破烂玩意儿,展会一开幕准跳闸,咱的展台一黑,假货摊就能趁虚而入,算盘打得比户部巷的豆皮还精。“你们的金属丝是用我们的防割面料熔的,” 陈军的铁链勒得对方手腕发红,跟酱肘子似的,“检测报告显示含镍量超标,接触皮肤会引发过敏,上周有个模特试穿后起的疹子,连片儿红得像洪山菜薹。”
订货会开幕当天,石十路带着十路盟的人堵住展台入口,活像群拦路抢劫的麻雀。他举着件结块的棉衣,对着围观的经销商大喊:“大家快看!楚记纱厂的棉衣就这质量,穿一次就成破烂!” 曲俊突然走上前,咔嚓一剪刀剪开棉衣里的填充物 —— 真棉衣的有机棉蓬松洁白,跟刚剥壳的莲子似的;石十路手里的假货里,全是缠成一团的渔网线,乱糟糟像汉阳兵工厂的废弃铁丝。
“我们的棉衣经过十二道蓬松处理,” 曲俊举起质检报告,纸页哗啦啦响得跟翻快板似的,“十路盟的假货用的是回收渔网,别说保暖,就是贴身都扎人,穿三天能把胳肢窝磨出茧子!” 他突然扯开假货的内衬,露出的金属丝在闪光灯下闪着冷光,“这种丧良心的做法,迟早会被市场淘汰,到时候连蔡甸的藕塘都嫌你们碍眼!”
石十路见势不妙,吹了声口哨想让埋伏在会场外的人动手,却被陈军的铁链缠住了脖子,勒得跟端午的咸蛋似的。混乱中,他怀里的账本掉在地上,泛黄的纸页上记着与八哥的交易 —— 用武汉的假货渠道,换取上海的走私线路,账本的最后一页还画着炸毁楚记纱厂的草图,时间定在冬至那天,倒挺会挑日子,是想给老织布机送终?
武汉警方的防爆犬在十路盟的防空洞搜出二十个燃烧瓶,瓶身贴着 “楚记纱厂专用洗涤剂” 的标签,里面的液体却是煤油和硫磺的混合物,闻着比吉庆街的臭干子还上头。石十路被押上警车时,突然对着长江大喊:“十路盟不会完的!我们在老字号协会的地基里埋了炸药,和你们的冬装样品同步引爆!” 这嗓门,不去唱汉剧真是屈才了。
曲俊立刻让陈军联系拆弹专家,在老字号协会的墙角果然发现了定时炸弹,引爆装置的感应器与我们棉衣的拉链材质一致。“他们在拉链上装了磁控开关,” 拆弹专家剪断引线,“只要有人拉动拉链,炸弹就会爆炸,这和九门堂在货轮上用的手法一模一样。这群人就这点出息,跟归元寺的鸽子似的,总惦记着老一套。”
冬至那天,楚记纱厂的老织布机织出了十路盟的通缉令图案,倒比印刷厂印得还精神。曲俊站在车间里,看着 1937 年的机器吐出的纯棉线,被缝进了老字号协会的第一批冬装订单里,线脚匀得像汉阳造的枪管纹路。“十路盟的一百个假货摊全被取缔了,” 曲丽的平板电脑上,市场监管局的通报正滚动播放,“石十路的表妹主动来我们厂当质检员,说要亲手撕掉自己缝的假标签。这觉悟,总算没丢武汉人的脸。”
陈军的铁链缠着枚新的奖章,是武汉商业联合会发的 “诚信经营示范单位”,背面刻着 “汉正街百年”。他指着窗外的长江,货轮正满载着楚记纱厂的棉衣驶向重庆,“老字号协会想和我们合作复原 1950 年代的工装,用楚记的老工艺,给长江上的纤夫做耐磨的外套。这才叫把钱花在正道上,比玩炸药强百倍。”
汉正街的灯笼在暮色中亮起,跟串起来的橘子灯似的。曲俊站在老字号协会的门口,看着陈军指挥工人拆除十路盟留下的假货摊,木板子扔得噼里啪啦响,像在放鞭炮。曲丽正给刚到货的棉衣挂吊牌,每个吊牌上都有个小小的二维码,扫出来是楚记纱厂的织布机在运转的视频,比抖音上的神曲还上头。“明年春天,” 曲俊望着长江上的落日,把江面染得跟打翻了的辣椒油似的,“我们要在江汉关建个纺织博物馆,让武汉的孩子都知道,这些老布是怎么织出来的,别长大了只认得网红直播。”
老织布机的轰鸣声在冬夜里格外清晰,像在诉说着武汉纺织业的百年故事,比评书先生讲得还带劲。曲俊知道,只要这台机器还在转,只要汉正街的青石板还在,新世纪传媒的天涯路,就永远扎根在这片土地上。陈军的铁链偶尔碰撞出火星,跟归元寺的香火似的;曲丽的笑声混着盘扣的叮当声,与长江的汽笛一起,汇成了属于武汉的商业史诗,比《黄鹤楼》的诗还耐听。
楚记纱厂的老织布机刚织出第一匹防汛服面料,长江大堤的防汛仓库就传来了麻袋撕裂的脆响,跟扯破棉絮的声音一模一样。曲俊捏着武汉文物局的奖章,指尖在 “文化传承奖” 的刻字上摩挲 —— 奖章的绶带里藏着根棕褐色线头,纤维结构与江防帮的徽记完全一致。这是武汉新冒头的帮派,由铁十二的小舅子水老鳖牵头,联合了十二联、十路盟的残余势力,在长江沿线的七个防汛哨所都安插了眼线,专做防汛物资的走私生意,真是连老天爷的饭都敢抢。
陈军的铁链缠在撕裂的麻袋上,袋口的防汛服面料泛着油光 —— 是被江防帮的 “浸油队” 做了手脚,这种面料混着废机油,遇水后会变硬,上周在试穿时,有个防汛队员的胳膊被磨出了血泡,跟被砂纸蹭过似的。“水老鳖的仓库藏在白沙洲的芦苇荡里,” 他用铁链撬开仓库的地板,下面的暗渠直通长江,跟老武汉的水网似的,“里面堆着三千件仿冒的防汛雨衣,帽檐的反光条是用回收塑料做的,夜里根本不发光,跟抹黑走路没两样。”
曲丽抱着 1960 年代的防汛服原件走进来,衣摆的补丁里嵌着颗生锈的纽扣 —— 是江防帮的标志扣,去年在十二联的假货里见过。“他们伪造了老字号协会的防汛物资采购单,” 她调出水利局的签收记录,有七批 “楚记纱厂防汛服” 其实是化纤混纺的假货,“水老鳖想在汛期来临前,用这些假货替换真货,等洪水来了,让我们的名声跟着大堤一起垮掉。这心思歹得,比夏天的馊面窝还臭。”
水老鳖的地盘在武昌的平湖门码头。他坐在艘改装过的冲锋舟上,船尾的防汛服堆成小山,每件的袖口都绣着 “楚记纱厂”,但针脚里的芦苇纤维暴露了底细 —— 是江防帮的 “捞尸队” 手工缝制的,这群人中有六个是十二联的老裁缝,最擅长仿冒防水涂层工艺。“曲总要是识相,” 他的蛤蟆镜反射着江面的波光,跟镀了层油似的,“把防汛服的独家生产权让给江防帮,长江沿线的利润分你两成,足够把东湖研学基地的玻璃幕墙再加厚三层。”
曲俊突然抖开件防汛服样品,下摆的开衩处露出暗缝,里面的防水膜已经开裂 —— 与去年在江防帮仓库查出的假货一致。“你们在防水涂层里掺了河泥,” 他指着样品的肩部,防水性能比标准低了 40%,“上周有个渔民穿了你们的假货,在江里打渔时雨衣渗水,冻得发起高烧,差点没救回来。你们这是在拿人命开玩笑,比跳长江还疯!”
水老鳖的脸瞬间涨成青灰色,跟泡了三天的藕带似的,猛地掀翻冲锋舟。藏在船底的砍刀滚落出来,刀柄缠着江防帮的棕绳,与三年前划破我们防汛物资运输船的刀刃纹路一致。“江防帮在长江有七十条走私船,” 他的声音像芦苇荡里的蛤蟆叫,聒噪得很,“从今天起,只要是楚记纱厂的防汛物资,每个码头都得交四成保护费!”
陈军的铁链如巨蟒般窜出,链环精准地锁住水老鳖的手腕,跟铐住螃蟹似的。他认出围观人群里的 “浸油队” 队长,那人正举着弹弓瞄准我们的面料样品,弹丸是用防汛服的塑料扣熔铸的。“你们在大堤的排水管道里动了手脚,” 陈军一脚踹翻旁边的假货摊,雨衣散落一地,跟被风吹落的荷叶似的,“上周那批真防汛服,就是被你们用带钩的铁丝勾破了防水膜,再污蔑是我们的工艺不过关。这把戏,比归元寺的算命先生还会忽悠。”
曲俊在芦苇荡的暗渠里发现了台涂着迷彩的缝纫机,机身上的楚记纱厂铭牌被泥浆糊住了一半 —— 是江防帮的 “快手队” 连夜改装的,去年在阳逻港的走私案中,这种机器查扣了五台。“他们想在汛期来临前,用这台机器赶制假货,” 他指着机腹里的暗格,里面藏着劣质胶水,“只要涂在面料接缝处,看起来和真的防水涂层一模一样,但遇水三小时就会失效,跟纸糊的一样。”
东湖研学基地的奠基仪式上,曲丽正指挥工人摆放防汛服展品,展架的钢管突然弯曲变形,跟被踩扁的易拉罐似的。检测显示钢管的承重系数比标准低了 30%—— 是江防帮的 “铁工队” 做的手脚,这群人中有八个是十二联的老焊工,最擅长在金属里掺废铁。“这些展架是水老鳖的表兄送来的,” 她用扳手拧开螺丝,里面的木屑混着芦苇纤维,“他们想在奠基仪式上让展架倒塌,砸坏防汛服样品,再让记者拍下来造谣。这心眼小得,比户部巷的鹌鹑蛋还小。”
陈军带着联防队员冲进江防帮的缝纫车间时,水老鳖的手下正往防汛服里塞稻草,跟填枕头似的。他甩出铁链缠住对方的缝纫机,链环弹出的微型检测仪显示,稻草里的霉菌孢子超标 —— 这种孢子会引发皮肤过敏,上个月有个防汛队员穿了他们的假货,胳膊上起了大片红疹,跟煮熟的小龙虾似的。“你们的胶水是用工业废料做的,” 陈军的铁链勒得对方指骨发白,“检测报告显示含有甲醛,长期接触会致癌,去年在江防仓库查获的假货里,就有二十桶这种胶水,毒得能药死江里的鱼。”
汛期来临前的物资检查会上,水老鳖带着江防帮的人堵住水利局的大门,跟群挡路的流浪狗似的。他举着件渗水的防汛服,对着围观的记者大喊:“大家快看!楚记纱厂的防汛服就这质量,洪水来了根本不顶用!” 曲俊突然走上前,将桶清水泼在真防汛服上,水珠在面料上凝成圆球滚落 —— 是用 1960 年代老工艺复原的防水面料,水老鳖手里的不过是件喷了劣质防水剂的假货,跟抹了发胶的假发似的。
“我们的防汛服经过七道防水处理,” 曲俊举起 1960 年的防汛记录,纸都泛黄了还透着股认真劲儿,“江防帮的假货用的是普通棉布,别说防水,就是小雨都挡不住,穿了跟没穿一样。” 他突然扯开假防汛服的内衬,露出的稻草在闪光灯下无所遁形,“这种拿防汛安全当儿戏的做法,迟早会被长江的浪头卷走,喂鱼都嫌你们骨头硬!”
水老鳖见势不妙,吹了声口哨想让埋伏在大堤上的人动手,却被陈军的铁链缠住了脖子,勒得跟戴了紧箍咒似的。混乱中,他怀里的账本掉了出来,泛黄的纸页上记着与水老鳖的交易 —— 用江防帮的走私渠道,换取十二联的假货配方,账本的最后一页还画着炸毁楚记纱厂织布机的草图,时间定在梅雨季节的第一场暴雨,倒是会选日子,想让机器跟龙王一起过节?
武汉警方的防爆犬在芦苇荡的暗渠里搜出三十个防水炸药包,外包装印着 “楚记纱厂防汛沙袋” 的字样,里面的炸药混着防汛服的纤维 —— 遇水后会加速引爆,这和江防帮在码头用的手法一模一样。水老鳖被押上警车时,突然对着长江大喊:“江防帮不会完的!我们在大堤的防汛哨所里装了定时炸弹,和你们的防汛服样品同步引爆!” 这嗓子喊得,比长江的浪头还凶。
曲俊立刻让陈军联系防汛指挥部,拆弹专家在三号哨所的防汛服仓库里发现了炸弹,引爆装置的感应器与我们的防水面料成分一致。“他们在面料里织了吸水纤维,” 拆弹专家剪断引线,“只要湿度超过 80% 就会引爆,这和江防帮在走私船里用的手法一模一样。这群人脑子里装的不是水,是炸药吧?”
梅雨季节的第一场暴雨来临时,楚记纱厂的老织布机在防汛仓库里织出了江防帮的通缉令图案,雨水打在机身上,倒像给机器洗了把脸。曲俊站在机前,看着 1937 年的机器吐出的防水面料,被缝进了长江大堤的防汛服里,针脚密得跟雨点似的。“江防帮的七十条走私船全被警方扣押了,” 曲丽的平板电脑上,长江航运的整治通报正滚动播放,“水老鳖的儿子主动来防汛服车间当学徒,说要亲手织出真正的防水面料赎罪。浪子回头金不换,总算没白瞎这手艺。”
陈军的铁链缠着枚新的奖章,是武汉防汛指挥部发的 “江防贡献奖”,背面刻着 “长江安澜” 四个字。他指着窗外的雨幕,穿着楚记防汛服的队员正在加固大堤,跟雨中的雕像似的,“老字号协会想和我们合作复原 1954 年的救生衣,用楚记的老工艺,给长江上的渔民做更安全的救生设备。这才是积德的事儿,比玩炸弹强万倍。”
东湖的研学基地工地上,暴雨浇不灭工人的热情,跟打了鸡血似的。曲俊站在地基旁,看着陈军指挥工人浇筑防水混凝土,泥浆溅得满身都是,跟刚从江里捞出来似的。曲丽正给防汛服的样品挂说明牌,每个牌子上都有个二维码,扫出来是 1960 年防汛队员穿着楚记纱厂雨衣的老照片,黑白的影像里透着股硬气。“明年汛期前,” 曲俊望着雨中的长江,浪头拍打着大堤,跟在打鼓似的,“我们要在大堤上建个防汛博物馆,让武汉人永远记得那些用生命守护家园的日子,别光知道看抖音刷快手。”
老织布机的轰鸣声在暴雨中格外有力,像在与长江的涛声共鸣,比交响乐还震撼。曲俊知道,只要这台机器还在转,只要长江大堤还屹立着,新世纪传媒的天涯路,就永远扎根在这片被水滋养的土地上。陈军的铁链偶尔碰撞出雨雾中的星火,跟黑暗里的灯塔似的;曲丽的笑声混着防汛队员的号子声,与长江的咆哮一起,汇成了属于武汉的生存史诗新篇章,比任何诗篇都更有力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