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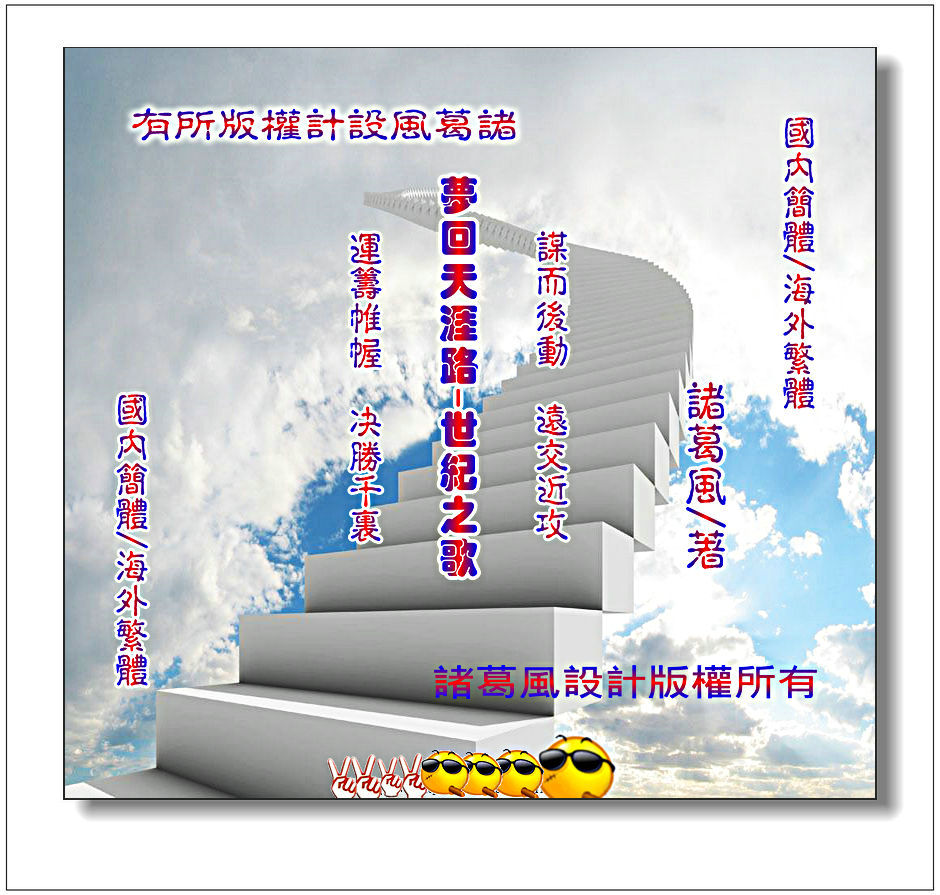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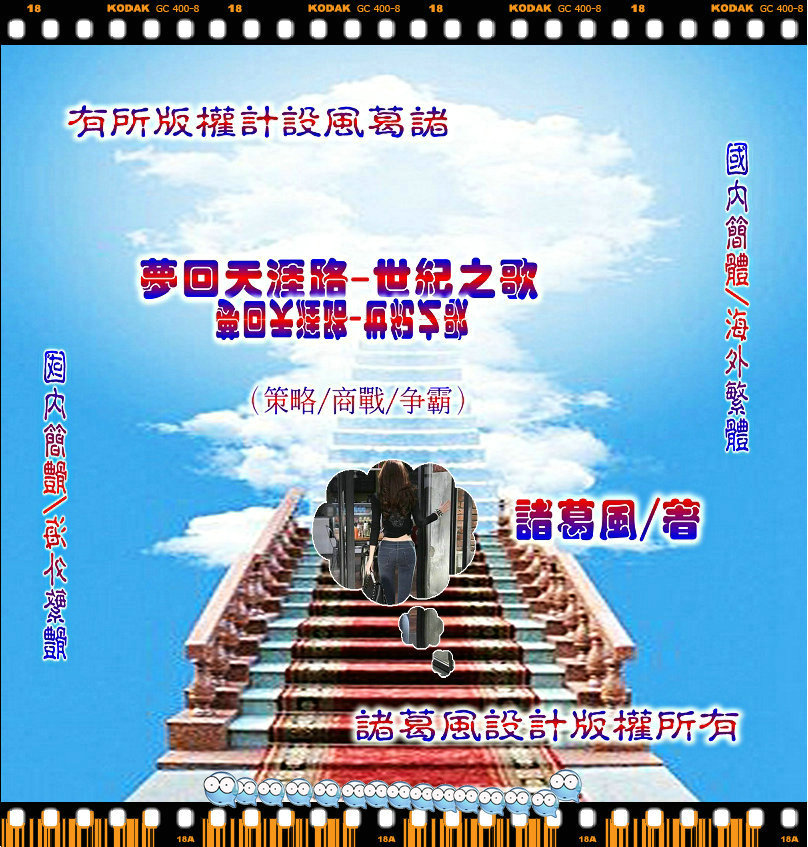
第一百四六章.盗亦有道
曲俊突然挥手示意渔民解开缆绳,一艘挂着楚记船帆的渔船缓缓驶入长江,江风鼓起的帆面在酸雨里泛着柔和的米白色,像一块浸在玉液里的羊脂白玉。“真船帆用了 1955 年的防水工艺,” 他的声音透过扩音器传遍码头,雨水顺着他的黑色风衣下摆汇成细流,在地面上织出一张透明的网,“能抵御 pH 值 4.0 的酸雨,而港联帮的假货,在 pH 值 5.6 的正常雨里就会溶解,简直是纸糊的玩意儿。” 他突然指向赵港生手里的样品,布面已经烂出三个洞,露出里面的塑料网,活像块破渔网。
港联帮的打手们突然从集装箱后冲出,手里的砍刀在雨水中闪着寒光,看着挺唬人。陈军的铁链如游龙出海,链环在空中划出银亮的弧线,每声脆响都伴随着一声惨叫 —— 他的左脚踩着块港联帮的假船帆,右脚蹬在个翻倒的油桶上,身体腾空时铁链横扫,瞬间将五个打手的刀卷飞,动作帅得能让江边的姑娘们尖叫。有个打手想从背后偷袭曲丽,被她甩出的铜梭正中眉心,梭子上的楚记商标在雨水中格外醒目,像是在给这蠢货盖个耻辱章。
混战中,赵港生想乘乱跳上停在岸边的快艇,跑得比兔子还快。曲俊眼疾手快,抓起码头边的一根缆桩铁链扔过去,铁链在他手中转了三圈,精准地缠住对方的腰,跟套住头野猪似的。他猛地拽动铁链,赵港生重重摔在防波堤上,嘴里的假牙飞出来,正好落在块楚记船帆上 —— 假牙的塑料材质与假船帆的纤维一致,遇水后都泛着股刺鼻的化学味,熏得人直皱眉。
“你的快艇油箱里掺了海水,” 曲俊的皮鞋踩在赵港生的手背,雨水顺着他的眉骨流进眼睛,让他睁不开眼,“港联帮的‘水鬼队’早就被我们策反了,他们说你承诺事成后,把武汉的码头都改成走私站,你这如意算盘打得也太响了!”
武汉警方的冲锋舟此时冲破雨幕,警笛声在江面回荡,像催命符似的。港联帮的打手们纷纷扔下刀投降,却被雨水泡软的假船帆滑倒,一个个摔得四脚朝天,狼狈极了。在地宫搜出的账册显示,他们三个月内就往东南亚走私了两千件假船帆,利润足够买下三艘赵港生的豪华游艇,真是赚黑心钱赚疯了。
赵港生被押上警车时,突然挣脱警察的手铐,对着楚记纱厂的方向嘶吼:“我叔叔在伦敦的船运公司不会放过你们!他会让楚记的船帆在泰晤士河变成碎片!” 他的嘶吼被雨声吞没,跟蚊子叫似的。左脸的蜈蚣疤因愤怒而扭曲,香云纱褂子被雨水泡得透湿,龙纹里的金线在警灯下发着惨淡的光,看着就晦气。
楚记纱厂的老织布机在雨夜里继续运转,织出的东南亚船帆泛着珍珠母般的光泽,漂亮得很。曲俊站在车间里,看着陈军用铁链测量船帆的张力,链环的刻度与 1955 年的标准完全吻合,分毫不差。“赵港生的叔叔赵英伦,” 陈军的声音带着雨水的湿冷,“在利物浦有个船用材料厂,据说想联合欧洲的黑手党,抢我们的地中海订单,真是不自量力。”
曲丽走进来,发梢的水珠滴在刚织好的船帆上,立刻凝成圆润的水珠滚落,像珍珠似的。她手里拿着份东南亚渔业协会的证书,烫金的文字写着 “最佳船帆供应商”,金灿灿的晃眼。“老字号协会刚才来电,” 她的眼睛在车间的灯光下亮如星子,“泰国、越南、马来西亚的渔民协会都想和我们签长期合同,他们说楚记的船帆是‘海上护身符’,这评价可不是吹出来的!”
武汉港的灯塔在雨后重新亮起,光束穿过薄雾照在一艘即将起航的货轮上,甲板上的楚记船帆在夜风中轻轻起伏,像展翅欲飞的大鸟。曲俊站在码头的钟楼前,看着陈军将铁链缠在锚链上,链环碰撞的声响与货轮的汽笛交织成歌,还挺好听。曲丽的笑声从海关大楼传来,她正用流利的英语向东南亚客商讲解船帆的保养方法,发间的珍珠胸针在灯光下闪着柔和的光,优雅得很。
老织布机的轰鸣声在晨光中格外清晰,像在诉说着一个关于坚守的故事,耐人寻味。曲俊的指尖划过机器上 “1937” 的铭牌,突然明白外公日记里的那句话 ——“纺织业的战场,不在账本里,在每根线头的良心上”,这话真是说到了点子上。此刻,陈军的铁链正轻轻搭在新织的船帆上,曲丽的钢笔在订单上签下名字,长江的水拍打着码头的基石,楚记纱厂的路,正从武汉的晨雾里,向更辽阔的海域延伸,前途无量啊。
楚记纱厂的老织布机刚织出第一匹地中海定制船帆,武汉港的雾笛就发出了悠长的呜咽,跟哭丧似的。曲俊站在汉街写字楼 18 层的落地窗前,指尖在伦敦码头的全息地图上停顿 —— 地图的泰晤士河模型里藏着一枚微型芯片,存储着赵英伦的黑手党联络网,这老小子藏得还挺深。此人右手缺失的小指处戴着枚铂金指套,指套上的蔷薇花纹由 32 道刻痕组成,对应着他控制的 32 个欧洲港口,真是狂妄得没边。左眉骨的疤痕呈锯齿状,是三十年前在利物浦码头被陈军的铁链划破的,现在想起来还疼吧。
陈军的军靴碾过武汉港的碎石滩,靴底嵌着的玻璃碴折射出彩虹色 —— 是欧洲黑手党 “蔷薇会” 做的手脚,这种船帆混着碎玻璃织成,抗穿刺性能比标准低了 80%,上周在马赛港,有艘渔船的帆被礁石划破,海水灌进船舱差点沉没,真是造孽。“赵英伦的货轮‘利物浦号’正泊在吴淞口,” 他用铁链撬开一个标着 “L-19” 的集装箱,里面的船帆堆里埋着楚记纱厂 1958 年的铁梭,梭身上的锈迹与蔷薇会的徽记纹路一致,“上个月有批发往巴塞罗那的防盐雾船帆,在途经直布罗陀海峡时被他们换了包,换成了化纤混纺的假货,海风一吹就散成条缕,跟破布条似的。”
曲丽穿着件香槟色丝绒长裙走进来,裙摆的暗纹是用楚记纱厂的金棉纱织成的,华丽得很。腰间的腰带突然松开 —— 里面藏着一根细铜丝,铜丝表面的蔷薇花纹在灯光下显形,又是这些小把戏。她的指尖捏着铜丝缠绕在钢笔上,铜丝立刻渗出黑色液体:“这种丝含砷量超标,” 她的睫毛在吊灯下投出扇形阴影,调出质谱分析图,黑色液体是黑手党的特制墨水,“三个月就能腐蚀船帆的经纬线,去年在赵英伦的走私帆船上见过,他们就不能换点新花样吗?”
赵英伦的私人游艇 “蔷薇号” 缓缓驶入武汉港,甲板上的侍者正用银盘托着香槟,摆什么谱。托盘的雕花与楚记纱厂的船帆商标惊人相似 —— 是蔷薇会的 “雕刻队” 用船帆铜模改的,这群人里有六个是港联帮的老工匠,最擅长仿冒欧式船帆的亚麻纹理,就这点能耐。他站在游艇的旋梯旁,一件深灰色羊绒大衣的领口别着枚蔷薇胸针,花瓣由楚记纱厂的老棉纱压制而成,遇热会散出苦杏仁味,还挺会装。“曲总年少有为,” 他的牛津腔裹着利物浦的粗粝,听着就别扭,左手的铂金指套在阳光下闪着冷光,“不如把地中海的船帆代理权让给蔷薇会,欧洲的利润分你两成,足够把楚记纱厂的老织布机镶上钻石,怎么样?”
曲俊突然抖开一件地中海船帆样品,纬线里的沙砾簌簌落下,与陈军带回的碎石滩样本成分一致,假货就是假货。“你们在船帆里掺了撒哈拉沙漠的石英砂,” 他的拇指按在赵英伦的蔷薇胸针上,胸针的温度透过布料传来,“这种砂在湿热环境下会膨胀,上个月在那不勒斯港,有艘渔船的帆鼓成球形,桅杆被压断砸伤了两个渔民,你们这是在杀人!” 他的深灰色西装袖口露出块银表,表链的链节与楚记纱厂的钢梭轮廓吻合,表盖打开的瞬间,里面的微型投影仪射出赵英伦与黑手党头目的合影,证据确凿。
赵英伦的脸瞬间涨成青紫色,猛地将香槟杯砸在甲板上,玻璃碴子溅得到处都是。玻璃杯碎裂的声响里,他的铂金指套在阳光下划出冷光:“蔷薇会在欧洲有四十个分会,” 他的锯齿状疤痕因愤怒而抽搐,看着挺吓人,“从今天起,只要挂楚记纱厂船帆的船进欧洲港口,每吨货物都得交‘蔷薇税’,不然就让它在大西洋喂鲨鱼,不信你试试!”
陈军的铁链突然从雾中窜出,链环精准地缠住赵英伦的手腕,让他动弹不得。他的右臂肌肉贲张如铸铁,铁链在晨光中绷成一道寒光,链环上的倒刺深深扎进对方的皮肉 —— 倒刺涂着曲丽研发的防凝血剂,在含盐环境下会加速出血,这叫自作自受。“你们在船帆的边缘织进了钢丝网,” 他的喉结滚动着吐出句话,左手扯过一块蔷薇会的仿品,钢丝网被拽出时带起一串火星,“去年在西西里岛,有艘渔船的帆被这种钢丝缠住螺旋桨,船身失控撞在礁石上,三个渔民失踪,这笔账迟早要算!”
曲丽蹲在蔷薇会的船帆堆里,指尖捻起一根泛着橄榄油味的线头,难闻死了。她的指甲涂着酒红色指甲油,用力掐进线头的结节处,线头立刻渗出乳白膏体 —— 是用地中海的橄榄油混合松香做的黏合剂,这种物质在 40℃以上会融化,上周在热那亚的仓库,有批假货因此粘成硬块,真是活该。“蔷薇会的‘胶水匠’里,有四个是港联帮的老工人,” 她突然掀起一块船帆,下面的防潮布印着楚记纱厂的老厂徽,却是用含铅染料印的,“这种染料接触皮肤会起水疱,昨天有个验货员的脖子已经烂了巴掌大的一块,看着都让人揪心。”
蔷薇会的秘密作坊藏在武汉的古琴台地宫,还挺会选地方。曲俊推开刻着 “高山流水” 的石门时,四十台织布机正在轰鸣,吵得人耳朵疼。织工们的后颈都纹着蔷薇花纹身,花瓣的数量与他们加入黑手党的年限一致,真是臭味相投。最里面的织机前,一个瞎眼老头正用手摸索着编织船帆商标,他的眼窝蒙着块黑布,布角露出的疤痕呈放射状 —— 是二十年前在利物浦码头,被陈军的铁链打中的,黑布的染料与赵英伦大衣的羊绒纤维一致,真是一路货色。
“这些船帆的抗紫外线系数只有我们的两成,” 曲俊拿起一块刚织好的样品,对着地宫的烛火举起,布面的经纬线在火光中显出断裂的纹路,“在地中海的烈日下晒半个月就脆得像饼干,一掰就碎。” 他突然将样品扔进旁边的盐水缸,船帆立刻浮起一层油膜 —— 是用蔷薇会的 “浸油队” 特制的鱼油浸泡的,这种油混合着地中海的海藻发酵而成,两个月就能让帆布腐烂出洞,真是恶心。
赵英伦的军师,一个留着络腮胡的矮胖男人,正用计算器计算着假船帆的利润,算盘打得真精。他的食指戴着枚骷髅戒指,戒面的空洞里藏着根毒针,针尖的毒液与楚记纱厂的棉絮颜色一致 —— 是用来伪造船帆检测报告的荧光剂,手段真够阴的。“曲总要是肯合作,” 他用袖口擦了擦滑到鼻尖的玳瑁眼镜,镜片反射着地宫的烛火,“我们可以在伦敦设个新世纪传媒的分公司,让您当名誉董事长,实际生意由蔷薇会说了算,您就等着坐享其成,多好!”
曲丽突然从计算器下抽出一本皮质账册,账页上的墨迹带着海水的腥气,难闻得很。她的指尖点在 “法国” 条目下,用红笔圈着的日期正是下周的欧洲渔业博览会,旁边画着一艘燃烧的船,船帆上标着 “楚记” 二字,真是居心不良。“你们想在博览会上,用我们的正品船帆做演示,” 她突然提高声音,账册的夹层里掉出个微型炸弹,“等船开到比斯开湾,就用这种藏在帆杆里的炸弹引爆,让船在各国代表面前爆炸,让我们出丑,没门!”
陈军的铁链突然缠住矮胖男人的计算器,按键散落的瞬间,他的左脚踩住对方的骷髅戒指,让他动弹不得。“这种炸弹的引信有蔷薇会的钢印,” 他弯腰捡起个按键,键缝里卡着根金色线头,“去年在巴塞罗那港,有艘演示船就是被这种炸弹炸毁的,船长至今还在医院植皮,你们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?”
欧洲渔业博览会的前夜,武汉港突降冰雹,跟老天爷撒豆子似的。曲丽站在楚记纱厂的车间里,看着老织布机织出的船帆在冰雹中依然挺括,而蔷薇会的假货样品已经被砸出无数小孔,像筛子似的。她的指尖划过真船帆的防砸涂层,突然发现一处细微的凸起 —— 是陈军用铁链刻下的暗号,提醒她注意蔷薇会可能在博览会的食品里下毒,真是心细如发。
博览会当天,赵英伦带着蔷薇会的人堵住武汉港的国际码头,又来捣乱了。他举着一块被冰雹砸烂的假船帆,对着各国代表大喊:“大家快看!楚记纱厂的船帆就是这种破烂,根本经不起地中海的风浪!” 他的假牙在喊声中松动,喷出的唾沫星子溅在旁边的意大利代表西装上,对方的深灰色西装立刻显出一块褐色污渍 —— 是赵英伦大衣上的橄榄油蹭的,真是丢人丢到国外去了。
曲俊突然挥手示意渔民解开缆绳,一艘挂着楚记船帆的渔船缓缓驶入长江,江风鼓起的帆面在冰雹中泛着柔和的米白色,像一朵盛开的白莲花。“真船帆用了 1958 年的防砸工艺,” 他的声音透过扩音器传遍码头,冰雹顺着他的西装下摆滚落,“能抵御直径 3 厘米的冰雹,而蔷薇会的假货,在直径 1 厘米的冰雹下就会破损,简直是纸糊的。” 他突然指向赵英伦手里的样品,布面已经烂出十几个洞,露出里面的塑料网,真是惨不忍睹。
蔷薇会的打手们突然从集装箱后冲出,手里的砍刀在冰雹中闪着寒光,看着挺凶。陈军的铁链如游龙出海,链环在空中划出银亮的弧线,每声脆响都伴随着一声惨叫 —— 他的左脚踩着块蔷薇会的假船帆,右脚蹬在一个翻倒的木箱上,身体腾空时铁链横扫,瞬间将六个打手的刀卷飞,动作干净利落。有个打手想从背后偷袭曲丽,被她甩出的铜梭正中太阳穴,梭子上的楚记商标在冰雹中格外醒目,像是在给他盖个死亡印章。
混战中,赵英伦想乘乱跳上停在岸边的快艇,跑得比谁都快。曲俊眼疾手快,抓起码头边的一根缆绳扔过去,缆绳在他手中转了三圈,精准地缠住对方的腰,跟套住一头肥猪似的。他猛地拽动缆绳,赵英伦重重摔在防波堤上,嘴里的假牙飞出来,正好落在一块楚记船帆上 —— 假牙的塑料材质与假船帆的纤维一致,遇水后都泛着一股刺鼻的化学味,熏得人头晕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