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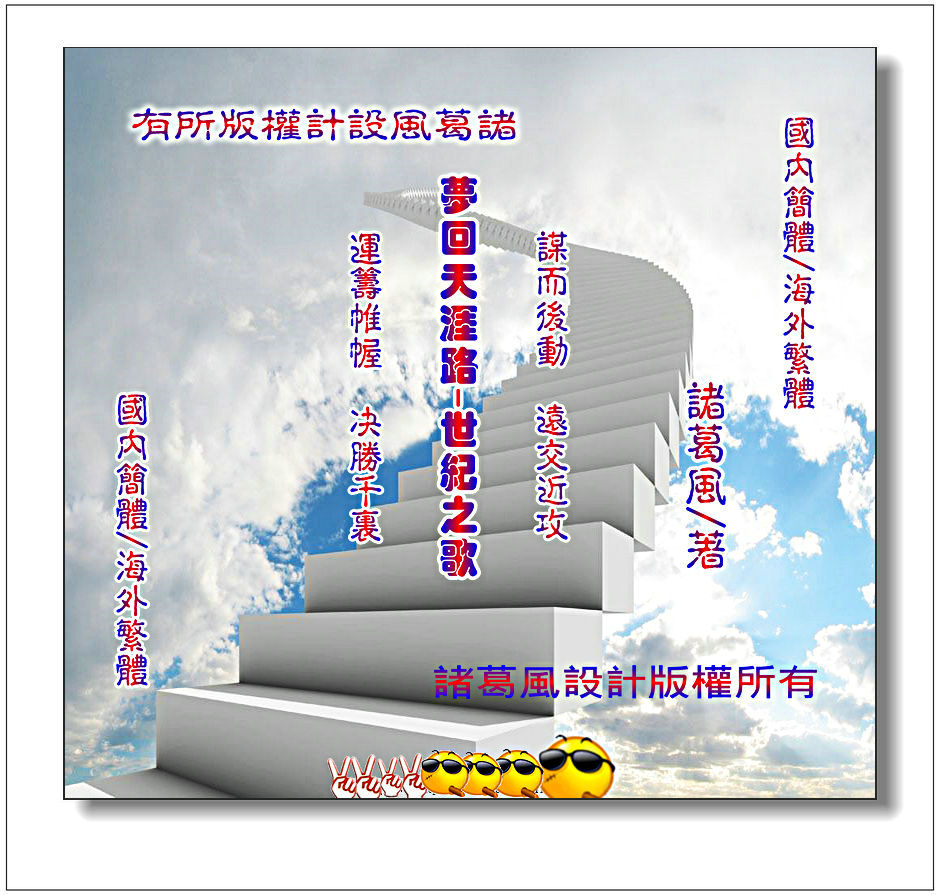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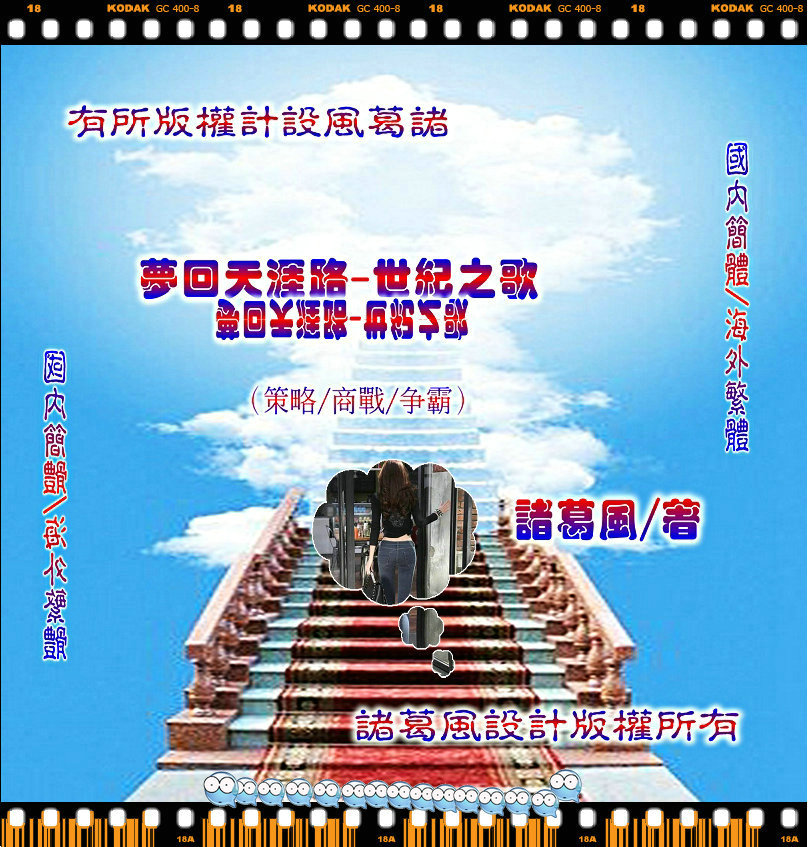
第一百六一章. 婊子牌坊
曲俊突然挥手让工人铺开楚记防油布,防油布在雨里平得像块镜子,工人拎起一桶原油泼上去,油珠子立刻滚得欢实,跟荷叶上的露水似的。“真防油布用了 2006 年的防油工艺,” 他的声音透过扩音器传遍码头,雨水顺着西装下摆淌成小瀑布,“各种原油都能挡得严严实实,石油帮那破烂,沾点油就跟海绵吸水似的。” 他突然指着石油财团负责人手里的样品,布面早被原油泡得透湿,一股子刺鼻味熏得人皱眉,跟打翻了馊水桶似的。
石油帮的打手们突然从集装箱后窜出来,手里砍刀在闪电下亮得晃眼,凶神恶煞的。陈军的铁链跟游龙出海似的,链环在空中划出银亮弧线,每声脆响都跟着砍刀落地的闷响 —— 他的铁链缠着块灭火器,对方扔来的燃烧瓶刚冒火苗就被扑灭,右脚同时踹翻旁边的沙土袋,沙土在地上铺出道防火线,玩得一手好战术。李强平时毛毛躁躁,这会儿却勇猛得很,抄起旁边钢管就朝冲过来的打手砸去,钢管跟对方的刀撞在一起,发出震耳的声响,跟敲锣似的。
严晓刚蹲在码头集装箱旁,手里的温度计对着燃烧的假防油布,跟发现新大陆似的。“这些防油布的燃点低得邪门,” 突然站起来对曲俊大喊,“石油帮的主力藏在八号仓库,里面藏了大量汽油,想一把火烧掉我们的防油布仓库,真是黑心肝!” 他说话时,眼睛亮得像揣了个灯泡,仿佛找到了天大的秘密。
混战中,石油财团的负责人想趁乱跳上岸边的快艇溜之大吉。曲俊眼疾手快,抓起码头边的缆绳扔过去,缆绳在他手里转了三圈,精准缠住对方的腰,跟套住头的野猪似的。他猛地拽动缆绳,石油财团的负责人重重摔在防波堤上,嘴里的金牙飞出来,正好落在楚记防油布上 —— 金牙内侧刻着石油帮的火焰徽记,跟假防油布的纤维成分一个模子刻出来的,真是不打自招。
“你的快艇油箱里装的不是汽油,是原油,” 曲俊的皮鞋踩在石油财团负责人的手背,暴雨打在脸上生疼也不管,“石油帮的‘火焰队’早就被我们策反了,他们说你计划炸掉武汉港的防油布仓库,让我们没法按时给中东供货,算盘打得噼啪响,可惜打错了!”
武汉警方的冲锋舟此时冲破雨幕,警笛声在江面回荡,跟催命符似的。石油帮的打手们纷纷扔下武器投降,却被地面的油污滑倒,摔得人仰马翻,狼狈不堪。从废弃油库作坊搜出的账册显示,他们三个月往中东走私了三万件假防油布,涉案金额够买七十艘石油财团的油轮,真是胆大包天。
石油财团的负责人被押上警车时,突然挣脱警察的手铐,对着楚记纱厂的方向嘶吼:“我表哥在北美的石油公司不会放过你们!他会让楚记的防油布在墨西哥湾变成碎片!” 嘶吼被暴雨吞没,跟放屁似的。左手手背的火焰状疤痕因愤怒更清晰,羊皮马甲被雨水浸透,口袋里的火焰形金章在警灯下发着惨淡光,跟他的下场一样凄凉。
楚记纱厂的老织布机在暴雨夜里继续运转,织出的波斯湾防油布泛着均匀光泽,跟镀了层油似的。曲俊站在车间,看陈军用铁链测量防油布张力,链环刻度与 2006 年标准完全吻合,分毫不差。“石油财团负责人的表哥北美石油商,” 陈军声音带着雨水的沙哑,“在墨西哥湾有个石油开采平台,据说想联合北美的石油黑帮,抢我们的北美石油订单,真是阴魂不散。”
曲丽走进来,发梢的水珠滴在刚织好的防油布上,立刻滚落下来,跟荷叶不沾水似的。她手里拿着份中东石油协会的证书,烫金文字写着 “最佳防油布供应商”,亮眼得很。公司女员工张婷性子活泼,笑着说:“科威特、阿联酋的石油公司都发贺电了,说楚记的防油布是‘波斯湾的守护神’,有了它,石油运输再也不用担心泄漏,这评价够高吧。”
武汉港的输油管道在雨后重新修复,新换的管道在阳光下闪银光,精神抖擞的。曲俊站在汉街写字楼露台,看陈军指挥工人搬运防油布,董千里在一旁核对数量,王忠修改新设计图,李强和郑勇检查码头安保设施,严晓刚蹲在地上研究新防油材料,各司其职忙得热火朝天。长江水依旧奔流不息,老织布机轰鸣声与城市喧嚣交织在一起,新世纪传媒的天涯路,在武汉这片土地上不断向前延伸,每一步都充满挑战与机遇,写着属于他们的传奇,这故事啊,还长着呢。
楚记纱厂的老织布机刚吐出第一米墨西哥湾定制防油布,武汉港的原油储罐就发出安全阀起跳的闷响,跟谁在暗处打了个闷嗝似的。曲俊站在汉街写字楼 18 层的合金地图前,指尖在北美地图的密西西比河口轻点 —— 地图突然浮起个骷髅头咬住油罐的图案,与北美石油商杰夫的 “海蛇帮” 标志不差分毫,活像鬼魂现了形。这家伙左胸的鳄鱼皮马甲别着枚铂金油井徽章,是 2008 年在休斯顿石油展上的冠军奖杯熔铸的,右脸刀疤从眉骨延伸到下颌,分明是十年前在新奥尔良码头被陈军的铁链划开的,此刻正坐在墨西哥湾的钻井平台上,用加密卫星电话指挥武汉的行动,电话那头,他的两个副手已经开始了无声的角力,真是窝里斗的一把好手。
陈军的军靴碾过青山的废弃油库,靴底裂缝里嵌着块凝固汽油弹残骸 —— 海蛇帮 “响尾蛇队” 做的记号,这种防油布混着汽油添加剂织成,抗燃点比标准低五成,上周在休斯顿港,有艘油轮的舱盖布被烟头引燃,烧掉了三个油罐,真是祸害人。“杰夫的集装箱藏在武汉港的保税区 B 区,” 他用铁链撬开个标着 “NA-119” 的货柜,里面防油布堆里埋着楚记纱厂 2009 年的钢梭,梭身刻痕与路易斯安那州的鳄鱼图腾对上了号,梭子旁边,躺着枚刻着 “汤米” 字样的黄铜子弹,“上个月发往加尔维斯顿的防腐蚀布,途经密西西比河时被他们掉了包,现在查明是杰夫的副手汤米干的,他想借此削弱卡洛斯的势力,真是玩得一手好阴的。”
曲丽穿着件银灰色风衣晃进来,风衣的内衬别着枚墨西哥银币 —— 币芯藏着根毒针,针尖倒刺在灯光下亮出海蛇帮的徽记,跟藏着掖着的坏心思似的。她指尖捏着银币在防油布上一划,立刻留下道灰黑色痕迹:“这种蓖麻毒素混了原油添加剂,” 眼睫毛在百叶窗的阴影里颤得像蝶翅沾了露,调出质谱分析图拍在桌上,“毒素在六十度会分解出神经毒,汤米的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仓库就用这招,毒死了三个卡洛斯的亲信,真是心狠手辣。” 她突然把银币扔在桌上,币缘的齿痕里卡着片鳄鱼鳞,“这是杰夫的贴身信物,现在出现在汤米的货柜里,内讧已经摆上台面了,正好让我们看场好戏。”
市场部赵敏抱着份受损订单进来,指甲缝里还沾着防油布的纤维,订单上的签名被咖啡渍晕染,隐约能看出是卡洛斯的笔迹,跟鬼画符似的。“海蛇帮在休斯顿的炼油厂瞎咧咧,” 她的声音压得极低,右手不自觉地按在腰间的手枪上,“说我们的防油布在原油浸泡下会释放毒素,其实是汤米故意往我们的样品里掺了重金属,卡洛斯已经派人来武汉想和我们做交易,这是想借刀杀人啊。” 她突然翻开订单的夹层,里面藏着张墨西哥湾的钻井平台分布图,“这是卡洛斯的诚意,他标出了汤米私藏假防油布的仓库,倒还有点脑子。”
质检部黄斌跟在后面,白大褂袖口沾着黑色油污,手里的检测报告上贴着三张照片 —— 第一张是楚记防油布在一百二十度原油中浸泡二十四小时的状态,跟新的一样;第二张是海蛇帮的假货三小时就溶解的样子,跟化了的糖似的;第三张照片里,汤米的副手正往假货里倒不明液体,鬼鬼祟祟的。“他们的仿品用了回收 PET 材料,” 他推了推沾满油污的眼镜,指着数据表格显摆,“汤米的批次比卡洛斯的多掺了三成的塑化剂,目的是让假货更快失效,嫁祸给卡洛斯负责的区域,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”
杰夫的 “海蛇号” 钻井平台模型摆在武汉港的秘密仓库,模型的钻杆里藏着枚微型摄像头,跟贼眼似的。汤米站在模型前,他的左手缺了根小指,是去年在争夺密西西比河航线时被卡洛斯的人砍掉的,此刻正用残指敲击着休斯顿的标记:“今晚把这批假货运到楚记的原料库,” 他的鳄鱼皮靴碾过地上的烟头,靴跟的钢钉在水泥地上划出火星,“让他们的防油布也尝尝溶解的滋味,到时候杰夫就得承认,只有我能搞定武汉的生意,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”
仓库的阴影里,卡洛斯的亲信正用手机录像,他的领带夹是枚蛇形毒针,针管里的毒液与汤米货柜里的一致,跟一个娘胎出来的。当汤米转身时,他迅速将手机藏进靴筒,靴筒里还藏着把锯齿刀 —— 这是卡洛斯特意从阿根廷带来的,十年前用这把刀劈开了三个叛徒的喉咙,真是个狠角色。
楚记纱厂的夜班突然响起警报,董千里的手电筒光束扫过原料堆,发现三卷标着 “楚记” 的棉纱里混着不明粉末,跟撒了把毒药似的。他用镊子夹起粉末放在燃烧匙里,火苗立刻变成诡异的绿色:“是硫化物,” 他的声音在织机的轰鸣中格外冷静,指挥工人隔离这批原料,“汤米想让我们的防油布在高温下释放毒气,王忠,立刻修改工艺参数,别让他得逞。” 他突然注意到最里面的织机旁站着个陌生工人,对方的袖口露出半截蛇形纹身,他不动声色地按下了紧急按钮,跟老狐狸似的。
王忠的铅笔在设计图上划出道新的曲线,眼镜片反射着电脑屏幕的蓝光,新的防油布结构图上,陶瓷纤维的比例从三成提高到四成五,跟玩魔术似的。“加入玄武岩纤维能抵抗硫化腐蚀,” 他突然抬头,发现窗外闪过个黑影,黑影手里似乎握着枪,“李强,通知安保部加强巡逻,重点是东边的原料入口,别让人钻了空子。” 他说话时,铅笔在图纸上无意识地画着蛇形,与海蛇帮的标志惊人地相似,真是巧了。
李强的对讲机突然响起电流杂音,他正带着三个保安检查围墙,杂音里隐约传来枪声,跟放鞭炮似的。当他冲到东门时,只看到两个海蛇帮成员倒在血泊里,他们的胸口都插着蛇形毒针,但其中一个的手里还攥着半张地图,上面用红笔圈着卡洛斯在武汉的藏身点 —— 江岸区的废弃加油站,跟标了靶似的。“是内讧,” 李强的手枪保险栓咔嗒作响,他的拇指在扳机上微微用力,“汤米的人被卡洛斯反杀了,这是借刀杀人,让我们替他们收拾烂摊子。”
严晓刚蹲在尸体旁,他的放大镜下,毒针的针尖沾着根金色头发 —— 与汤米的发色一致,但针尾的刻痕却是卡洛斯帮派的标记,跟打了个明牌似的。“这针是汤米的,但下毒方式是卡洛斯的手法,” 他突然用镊子翻开尸体的眼皮,眼球上有细微的针孔,“他们在互相嫁祸,想借我们的手除掉对方,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” 他的指尖在尸体的口袋里摸到块口香糖,包装纸上印着墨西哥湾的地图,某个钻井平台被打了个叉,跟标了死刑似的。
